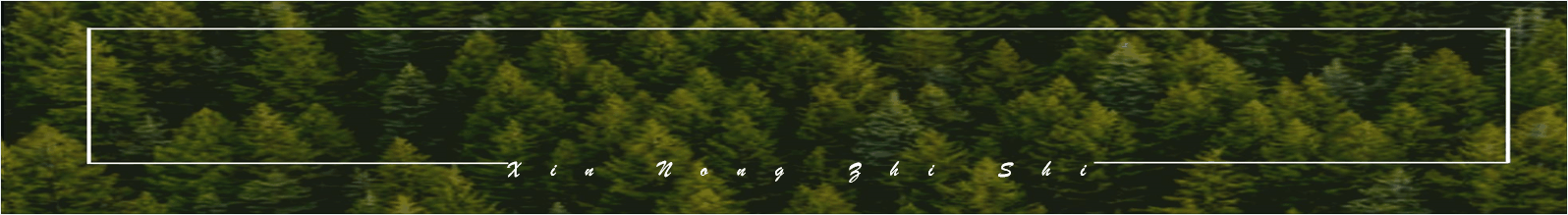马原的小说
对形式的迷恋是一个先锋小说家的存在标记。但对其他的作家来说,形式是否就不重要呢?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强调内容,认为形式仅仅是为内容服务的,没有内容,形式根本不能独立存在。但在20世纪小说写法的千变万化中,形式往往已经成为内容,或者说形式就是一种内容。先锋从本质上讲是拒绝现实与主流的,先锋是一种自由,先锋是一种精神。先锋派小说对现代汉语的结构规律与审美属性的探索达到了一个空前成熟的境地。但对语言自身的过度迷恋可能也限制了它对超越性世界的关注与表达。这是一种两难的处境,但真正的大师便是在这两难的处境里有着行走自如的能力。写作就是一种冒险,规规距距的文字是耐不住岁月的侵蚀的,异端的美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后来者所发现,文学史同时也是发现史。马原在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的女神》确定了他的叙事方式,而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则表明马原的叙事圈套完全圆熟。马原在《冈底斯的诱惑》里叙述三个不相干的故事,但是在叙述过程中马原极力制造这三个故事是有内在相互联系的某种假象,显然,这种“联系”使人觉得其中隐含着某种不可知的秘密。马原叙述过程是制作错觉,他在描写“天葬”的时间,先写到“死亡”,然后绕了一个圈子,使你觉得“天葬”是多么神秘。而事实上,马原并不直接进入叙述对象的“神秘”,甚至,他对“对象”的具体存在都未必感兴趣,他在意的只是叙述的方式。与马建被批判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相比,马原的重心在于如何叙述,而马建则是一种展览式的猎奇,他的小说是以纯粹的性主题撕去了掩盖在人类肉体上的文明遮羞布。马原一方面专注于他的“叙事圈套”,另一方面却用大量稀奇古怪的经验来填充他的圈套,造成一种反讽的效果。事实上无论过去多少年,重读马原,譬如重读他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拉萨的小男人》的系列作品。仍然只能无可奈何地说——它们是当代小说中最令人惊异的小说。最令人惊异的,是作者的想象力,他的写作技艺,和他的小说所提供的种种可能性。马原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创造了现代“汉语小说”的一种写法,确立了现代“汉语小说”的一种形式。而在此之前,这种写法和这种形式,在现代汉语写作中是没有的。但马原决不仅仅是一种小说形式的开创者,他在艺术上的博大与丰厚也是其它小说家所难以企及的。马原对自己的小说有着自信而深刻的认识,曾经在一篇七千字的名叫《小说》的文章里,马原用异常明确的文字表达出他的小说观念与小说理论,他对近世世界小说家的评价和对自己的小说的解释。“我就是哪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马原小说《虚构》中的第一句话)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样的句子时感受到的那种简练直接和对于操控一个故事的自信。那时我就敢肯定,这是一位不错的小说家。在马原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对传统的经验秩序的强而有力的质询。通常小说含有故事,阅读一部小说就是追随某种发展。但马原却拒绝传统的故事讲法,而是以苦心孤诣构造的叙事方式,以无所顾忌的诗性祈祷,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最尖锐的艺术表现方式。
金庸的小说
二十世纪汉语小说,首推金庸。金庸并非只是写下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武侠小说的那个个别意义上的作者,他还使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成为可能。金庸确立了新派武侠小说这种话语方式的丰富性与包容性,并影响了古龙、温瑞安、萧逸、卧龙生、诸葛青云等几乎所有的武侠作者。就此而言,金庸“作为作者的作用超出了他的作品的局限,使某些以他的作品为模式的相象和类似的因素进行循环——各种独特的符号、人物、关系和结构可以纳入其他的作品。”难怪学者冯其庸把金庸小说誉为“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从小说文本来看,金庸确实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他自己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金庸借武侠小说这种“古代形式”的创作,其实是当代境遇、现代心态的重新书写。借助于复杂错乱的时序、古代人物的装束与品格,掺合着现代人的孤独、焦灼与渴望,构建出一个怀旧式的侠义之邦。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不同于卢卡奇所美化的希腊式的“史诗世界”,即那个葆有“完整文明”的世界,而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破碎世界,带有现代性的创伤记忆。现代小说的主角是一个“有问题的个人”,是一个寻求者。然而小说的主角最后可以“瞥视”到意义的光芒,但这光芒却不能穿透现实,改变现实。具体到金庸的作品,它所呈现的是一个“有问题的个人”遭遇一个有问题的世界:《书剑恩仇录》是恢复汉室江山的使命与陈家洛个人情感的冲撞;在《雪山飞狐》以及“射雕三部曲”是雪洗父仇、个人成长的艰难历程。学者陈平原认为:“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写梦’与‘圆梦’只是武侠小说的表面形式,内在精神是祈求他人拯救以获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局限性。”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往往曲折书写并宣泄着乱世情结所深藏的焦灼和不安,它们构成一个纷繁交错的政治空间,以及爱恨交织的情感世界。这种政治空间以江湖的身份缓缓展开,自成一统,形成兰波所言的“在别处的生活”,以及保罗·利柯所指出的“不仅仅是现实之外的梦境”,是借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个新现实”本身。然而正如任大小姐所说的那样:“江湖风波险恶”,纵然是“在别处的生活”,依然照耀着现实的血腥影子。于是乎《天龙八部》里的萧峰厌倦了江湖的暴力、段誉厌倦了杀人的武学,《笑傲江湖》的令狐冲厌倦了对权力的膜拜与痴迷,《连城诀》里的狄云厌倦了金银财宝的贪婪。他们逃避于宏大叙事的包裹之中,成为试图超越历史、民族、国家的旁观者和局外人,他们最终选择的是个人的自由。正如葛兆光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他们更注重内心对理想世界的领悟和领悟中得到的快感,而不是外在于人的理想世界本身。”
残雪的小说
重读残雪的小说,依然惊讶于她对“恶心、丑陋、猥琐”的复制,在这种复制中我们看到的是“恶之花”与“罂粟之美”。然而“恶心、丑陋、猥琐”仅仅是阅读者的自身感受,残雪小说世界里的人物自己却对此毫无感知,他们经受着完全不同的体验:恐惧。恐惧才是残雪小说的核心。一切皆因恐惧而生,一切皆生恐惧。法国思想家蒙田说过:“恐惧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难忍受。”残雪在昭示侵害和否定产生恐惧的同时,也描述了笔下的人物对恐惧的反抗与逃避。但一切都是宿命,命定的厄运不可逃脱。不管是江水英钻进笼子不出来(《黄泥街》)、虚汝华把自己禁锢在钉上铁栅的小屋里阻挡他人的侵入(《苍老的浮云》),还是“我”呆在盖上盖子的大木箱里(《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都无济于事,无法获得心中渴求的安全感。这种无边的恐惧弥漫在残雪的小说之中,神秘而阴暗。1986年11月,残雪的中篇小说《黄泥街》发表,这条凭空制造的黄泥街几乎成了日后残雪小说世界的代名词,也是她观察人性的实验场。处女作《黄泥街》的故事,作为一个实际中有或没有都不确定的过去的故事,不,是作为“一个梦”讲述的,意在挖掘一个肮脏丑恶的世界,仿佛一首地狱里的温柔之歌。此后短短两三年,《苍老的浮云》、《山上的小屋》、《美丽南方之夏》、《天堂里的对话》,以及长篇小说《突围表演》,把一个陌生响亮的名字带进了文坛。“我的母亲化作了一盆肥皂水。”这是残雪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的第一句话。这篇作品无疑“具有浓烈的表现主义风格”,预示了残雪小说的走向与以后的写作历程,女性的隐秘体验与独特的写作表达让习惯了以往的阅读经验的读者目瞪口呆。正如美国《纽约时报》上的一段评论:“中国女人(指残雪)写的这些奇妙的使人困惑的小说,跟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几乎都没有关系。实际上,它们令人想起的是,艾略特的寓言、卡夫卡的妄想、噩梦似的马蒂斯的绘画。”残雪的小说是真正的现代派作品,与以前的作家不同,她不是停留在意识的层次上,更多的是写人的潜意识,她的小说没有笨拙的模仿,没有矫情作态的浅薄卖弄,一切都是从心底喷涌出来的真性和真情,她是靠先天的气质投向超现实主义。读残雪的小说,总会感受出人性的“恶”来。“恶”是残雪小说始终不变的主题。其实,正是在对恶的正视和解剖中,才会真正表现出对“善”的向往和向慕,透过苍老的浮云,我们才会体味出青春的振奋。
莫言的小说
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首发《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写的非常棒。这篇小说以“现代进行时”的描述方式表现农村的现实生活。单纯得几乎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的故事,却被作者写的色彩斑斓,充满声、光、色、影的迷离,展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象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象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正如谢有顺所言:“他早期发表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我尤为推崇,我觉得这是天外来物般的作品,那种通透的感觉、偏僻的角度、观察小孩的精准,已不可再得。”后来的《红高梁》亦是相当精彩的作品,以童稚观点回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对题材的处理体现出对传统小说叙事的叛逆,以追忆的姿态讲述历史。《红高梁》及其系列作品《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的成功,让莫言成为山东高密乡的代言人。以其生花妙笔创造了一个既写实又迷幻的乡土,他笔下的山东高密,其实只存在他的想象中,那不是历史上或现实里的乡土,而是他凭借着一己的文学壮笔,重新塑造的一个家乡,一个比历史或现实里的家乡,都要更精采更复杂更丰富更迷人的虚构的家乡,一个许多人都能理解认同的奇幻家乡。说到写作的能力,不少作家能够写出好作品,但不能持续写出好作品。莫言是一个例外,从1985年的开始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天堂蒜薹之歌》,到1989年的《酒国》,1995年的《丰乳肥臀》,2001年的《檀香刑》,2003年的《四十一炮》,2006年的《生死疲劳》,2009年的《蛙》。莫言一步一个脚印地写出了乡土中国近30年的历史和命运,作品里面饱满的“中国性”让他成为世界文坛的关注焦点。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一样,充满了象征和寓意。吸取欧美文学的创作经验,是中国1980年代那批作家的必经之路。但更为重要的是,中西文学的碰撞,促使莫言“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时事以魔幻写实手法冶于一炉”,促使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写出富有张力、情感饱满的农村“民间深层经验”,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莫言笔下的高密乡村,对于我们来说有一种触手可及的质感,仿若那一片片灿烂奔放的红高粱地,让人过目难忘,甚至能够闻到其中的泥土气息。莫言建筑了一个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乡村,莫言的高密乡充满原始的生命力、野性的思维、对命运无常的悲悯,它触摸到了意识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重新发现和复苏了中国民间的文化传统,民间的想象和力量,以一种接近变形的方式展现出来,放荡风流,地气饱满。
韩少功的小说
作家韩少功先生曾经在一篇《灵魂的声音》的随笔里这样谈到小说:“小说只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韩少功是极少数的能够在小说原创与理论思想之间游刃有余的作家,正如法国汉学家安妮·克琳女士所说的那样:“韩少功既是地方性的,又是世界性的。”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韩少功的小说世界由寻根而开始,虚构出一个人性复杂、光怪陆离的文字空间。譬如在他的早期获奖小说《西望茅草地》里。作者就试图写出生活的复杂和人物的多面。当韩少功连续抛出《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说佳作时,一个成熟的作家站在了读者的面前。《爸爸爸》是叙述一个部落失败历史的寓言,是对失落的父性、阳性的呼唤,同时也是对“妈妈性”的咒骂,幽默中透露着苍凉,对此日本文学评论家近藤直子说:“这是一篇令人恐怖的小说” 。《女女女》则是对自然人性的呼唤,也是一次女性精神的探险,对读者来说也是一次毛骨悚然的精神旅行。作家蒋子丹有如此评价:“不管是《爸爸爸》对国民劣根性痛心疾首的关注,还是《女女女》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审视,抑或《归去来》对人生世事飘忽不定的感觉,无一不浸透着对传统精神传统道德传统思维方式的悖反情绪。”事实上,在韩少功早期的小说叙事中,有着对中国农业文明中近亲繁殖可能产生弱智的内在恐惧,他发现了“现代性”背景下的中国农民,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坏死(譬如《爸爸爸》中的丙崽,直到后期的《马桥词典》,他关注的依然是现代性背景下农业文明的符号秩序混乱的问题)。1985年开始,韩少功重构的小说世界包含两个层次:隐性的和显性的。显性层面奇奇怪怪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索解须深入到隐性的层次,此时此刻流露的是作家独有的怀疑精神。在韩少功的世界里,显性有时表现为对隐性欲望、本能的掩饰,更多的时候则是被压抑的欲望、本能的变态化外显,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韩少功所塑形象为什么多为“畸人”。对“畸人”命运的强烈关注,让小说脱离了简单的写实层面,进入人性残缺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从最初简单的对弱势的关怀上升到对人性的悲悯与拷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王德威先生认为:“韩少功的世界是个阴森古怪的渊数,而这一想象的资源,与其说是来自西方文学,更不如说是遥指志怪及楚神话传统。韩少功最好的作品多以文革为题材,但他超越了伤痕文学的狭窄历史视野,为劫后的中国注入一末世景观。他从中国的现在看到了过去,又从中国的过去看到了现在。”
苏童的小说
对于苏童,我有一种难得的好感。中国当代作家,能入我法眼的并没有几位,苏童是其中的一位。曾经在广州的天涯,做过苏童的现场访谈,印象很好。苏童早期以中短篇小说赢得盛名,譬如他的《红粉》、《妻妾成群》、《1934年的逃亡》、《仪式的完成》、《已婚男人杨泊》。《仪式的完成》精彩绝伦,显示出苏童在短篇小说上的实力。民俗学家意外的死亡完成了仪式,命运的不可抗拒性揭示给读者,冥冥之中,生命的无常与诡异让我们无所适从。这就是“仪式的完成”的最后效果,意味深长。《已婚男人杨泊》有后来新写实小说的影子,但明显带有苏童的叙述风格——浓郁的诗意与行云流水的语言。至于《红粉》、《妻妾成群》、《1934年的逃亡》展示了苏童不可遏止的虚构才华以及对腐朽的过去时光的惊人想象力。“妻妾成群”精致地复制出古老宅院里的青春虚掷的悲剧以及女性互相伤害的人性挣扎,用虚构的笔墨为我们提供了栩栩如生的江南女人的隐秘世界,他全凭想象的力量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妻妾成群》是一部关于历史颓败的寓言,它传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废墟感,一种典型的世纪末感受。《妻妾成群》通过“性”来隐喻一个家族的衰亡,以一种极其感伤的情调,精致地描写旧社会的家族生活。小说背后的美丽哀伤,江南写作特有的湿润、柔美从深宅老院里散发出来,迷离恍惚,让人惊艳,让人忧伤。读这样的虚构作品,让人想起福科的一句话:“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虚构是一种力量,借苏童的笔墨,让我们重返1934年,重返解放前。后来苏童在长篇写作的领域里推出《我的帝王生涯》、《菩萨蛮》、《碧奴》、《黄雀记》。《我的帝王生涯》以优美的文辞虚构了一个帝王的一生,而在这个帝王的一生,又浓缩了历史上许多帝王的经历,写来轻灵跳跃,有一种强烈的对比感与虚无感。作者还特别告诉我们,不要将它当作历史小说来读。曲折的故事,藏着深深的玄机,以对自身的消解和对历史的虚构来完成想象历史的终极目的。苏童的很多小说,都聚焦在香椿树街,这条街上所发生的故事,皆被苏童写入笔触里,在绝望里透散生命的野性。那些男男女女,带着命中注定的宿命,一步步走向深渊。天意如此,作者却以一种唯美的文字写出来,强烈的对比推进了悲剧的重量。纵然阳光灿烂,读苏童的小说,依旧有一种阴森的冷浸入肌肤。
慕容雪村的小说
当痞子蔡的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被当做网络文学代表作的时候,天涯社区的版主慕容雪村2002年4月在舞文弄墨贴出了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很快得到网友的追捧,人气极盛,几乎所有论坛都转贴了这部长篇小说,阅读量迅速超过20万次,创造了网络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以后的时间里逐渐成为网络文学的经典作品,慕容雪村本人也成为天涯社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貌似通俗,却在写作的原始状态里表达生活的真相,写得肆无忌惮,将生存的残酷,现实的灰暗、人性的丑恶表露无遗,淋漓尽致。作为小说江湖的世外高手。雪村兄的语言有如剃刀般锋利,庖丁解牛,痛快淋漓。他的叙事直入人性深处,在金钱与爱情的炼狱中,窥见坚实的真情实感。“我从肉欲的高山上滚落下来,表情如圣徒一样神圣和沧桑。世界一片虚空,我静静地躺着,身下潮湿,心中宁静,目光忧伤。”这种虚无感,绝望的挣扎令人惊心动魄。《原谅我红尘颠倒》还是慕容雪村的一贯风格,写出物欲横流之下红尘男女的喜怒哀乐,笔墨痛快淋漓,隐含着作者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悲悯。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群人模狗样的律师及政法机关的公务员,由他们的行为展现这个社会深入到骨子里的腐烂。没有干净的手,没有所谓的正义,一切只不过是利益的争夺而已。正所谓:恨水萧萧西风冷,满城衣冠禽兽。慕容雪村的写作脱离了网络写作常有的快餐式毛病,还原为一种对人生、社会的内在批判。无论《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抑或《原谅我红尘颠倒》,皆非商业网文的书写,带着疼痛,带着创伤记忆,凝注个人性的批判。所以才有后来卧底传销,写就《中国少了一味药》的非虚构作品。可以说慕容雪村的写作挽回了网络文学的尊严,恢复了文学原初的价值。
阿城的小说
最早读阿城的作品乃是他的小说集《棋王》,作家出版社于1980年代推出的文学新星丛书之一。《棋王》收录了阿城小说的几部代表作,譬如“棋王”、“孩子王”、“树王”。其中“树王”一篇稍弱,“棋王”与“孩子王”绝对是神品,入世近俗,贴近地气,不可轻易看过。“棋王”开篇第一句:“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点出时代背景,借王一生这个知青的棋道讲述人生之意义。这其实是一方面,小说的另一方面又借“吃”写出民以食为天的文化内涵。王一生对“吃”的庄重态度,起源于饥饿的古老记忆,小说由此俗中见雅,隐秘传达了一个民族的过往记忆。《棋王》的叙事明显带有古代话本的叙述技巧,有张有驰,遣词用句精彩绝伦,有地域色彩又超越地域色彩,上升为“道”的境界。《孩子王》则是“教育以识字始”的春风化雨,惟在特殊年代,彰显出深远的价值。小说里王福的作文“我的父亲”,隐约传达出《孩子王》的意蕴。已故的评论家胡河清对阿城的“三王”很是认可,以为“棋王”在承载道家文化智慧的同时又隐含着对人格美的追求,立足于东方传统文化而又赋予了现代精神。阿城后来的“遍地风流”系列,仿佛笔记小说,遣词用句皆有风味。譬如“峡谷”一篇写鹰“那只鹰又出现了,慢慢移来移去。”移字用的极妙。这些小说,文字都短,意味却浓,飘逸空灵,可以细细品鉴。至于他的《威尼斯日记》、《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等随笔集,意思依旧在,看得出原创的才气隐隐透散。然毕竟跟小说的价值差了许多,杂色亦是色,却比不得纯色的正大光明。就好比说,常识与通识里的那些意思,有的人也能写出来。但是,小说《棋王》只有一篇,别人万万写不出。另一位作家王小波亦是如此,他的随笔也是常识,写的确实很好,但并非独一无二,别的人也能写出来,而王小波的某些小说真正独一无二,属于自己的精魂。读阿城的访谈,觉得他真是一个好人。跟记者说到另一位作家王朔,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坏毛病,对王朔的人与文满口称赞。只是可惜阿城为什么不写小说了,就算是为稻粱谋,也不必完全放弃虚构啊。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与命运。阿城就算只有《棋王》一篇,亦足以传世。
刘慈欣的小说
重读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以往的看法略有一些改变。第一次读《三体》,觉得想象力丰富,其宇宙文明生存法则的设定亦符合我的想象。不过作为硬科幻,可读性上还是有些欠缺。譬如文革的书写,一方面加深小说的历史厚度与批判性,但同时亦是对科幻的疏离。然而重读《三体》,理解加深,又觉得可读性亦有不可忽视之处。三部小说必须连读,合而为一,方能见出作者心中的城府,所谋乃大。由具体的文革历史,带出三体世界与人类的空间争夺,笔力所及,乃至宇宙与星际,想象极其丰沛,浩汗无涯。人类一直期盼外星文明,其实外星文明真的降临地球,可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在更高文明的俯视之下,地球上的人类可能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眼中的蝼蚁,其生存死亡完全不值一提。《三体》辉煌无比,但刘慈欣的很多短篇亦是科幻小说里不可多得的佳作。我先读的乃是刘慈欣的《2018》,近年来,大刘在科幻创作里水涨船高,风头一时无两。《2018》属于短篇小说集,收十三篇。不过都不是新作,最新的“2018”写于2010年,最早的“鲸歌”写于1999年。在刘慈欣的《三体》里,多少都有他的短篇小说的痕迹,其中“超新星纪元”还改写为长篇小说。读完之后,觉得“诗云”最好,它提出一个极有意味的命题:极致的科技是否能够创造一切,包括艺术?作为阅读的过程来说,读过《三体》,再读短篇小说集《2018》,多少有些失落。毕竟厚重的《三体》展现了本土科幻的辉煌,提升了中国科幻的水准。而《2018》由于短篇自身的局限,注定了不能写成荡气回肠的星际传说。令人关注的是,大刘在展现科幻想象力的同时,亦不忘探讨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以及更加深远的,对人性、道德等精神领域的触动。或许,他之前的短篇书写,就是为了成就《三体》的凤凰涅槃。科幻文学在中国一向寥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科幻小说甚至被官方定义为“毒草”,令刚刚萌芽的科幻创作一蹶不振,幸存者苟活在民间。此等惨痛,对于五四起就倡导科学与民主之中国,尤令人扼腕。
孙甘露的小说
重读孙甘露的小说,依旧会被他的写法所震惊。他的自言自语,他的一意孤行,乃是当代语言最激进的挑战者。孙甘露把写作变成一次“反小说”的修辞游戏。他的故事既没有起源,也没有发展,当然也没有结果,叙事不过是一次语词放任自流的自律反应过程而已。但文辞优美,仿佛读一首诗或一篇散文,随着作者的笔墨一直向前,一直向前,最终抵达文字的虚无之境。他的成名作乃是《访问梦境》,仿佛命中注定,孙甘露的小说真的是访问梦境,给人以梦的迷离与碎片化的模糊。再看看他的小说标题,譬如《请女人猜谜》、《信使之函》、《我是少年酒坛子》、《仿佛》、《夜晚的语言》,隐隐约约的诗意流淌,若有若无的片段记忆,让人想起诗人但丁的一句话:“我见到的幻像,几乎完全消失,但从中诞生的芳香,依然一点一滴落在我心中。”在《信使之函》的开头,孙甘露引用了卡夫卡的一段话:当然,他不过是一个信使,而且不知道他所传递的信件的内容,但是他的眼色、笑容以及举止似乎都透露着一种消息,尽管他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对此,已逝的天才批评家胡河清认为“也许这就是孙甘露的自画像”。信使从现实远方赶来。从那无从详尽转述的时光的某一刻出发。此刻,初始的印象已从远处走向我记忆的近端。所有在我之前的行走已和我的行走涓流般汇成一体(《信使之函》)。事实上,孙甘露的小说中,已经没有传统现实主义里的典型人物甚至普通人物,他的小说人物几乎若有若无,以镜像式的生存方式存在着,没有一定的性格,缺乏完整的形象,缺乏确定的心理和稳定的行为动机,其生物性和社会性特征流失在了语言本性之外。他们成为语言的一个借口,语词的暂时停泊之地,字与字之间的通道而已。从某种意义来说,孙甘露的写作是一种无指涉的虚构,一种词语的狂欢。其精神依据便是法国新小说叙事的物化写作,契合九十年代的时代风尚,在一大片传统式写作之林里傲然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