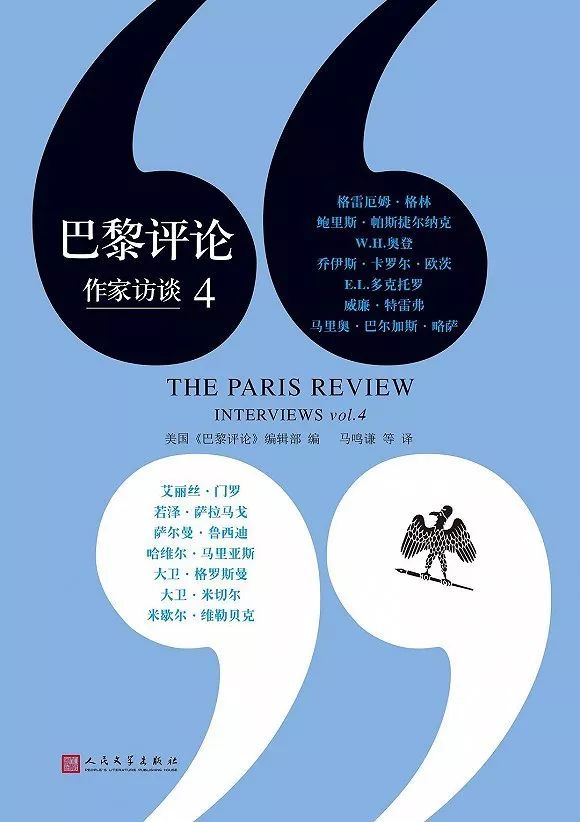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 黄昱宁 等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作家访谈”第四辑出版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梳理了部分写作经济问答与读者共享,这些问题一方面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些伟大的作家和当时的文学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作为现实文学生态的对照,因为这些讨论在当代中外作家的访谈中仍然不断回响。
记者和教师:
哪个职业更容易出作家?
许多作家都做过记者或是教师,至于这两份工作是否对写作有益,他们持不同意见。
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从事新闻业多年,他每个星期为报纸撰写一到两篇新闻文章,这些文章并没有那么强的新闻性,而更接近于五花八门的杂志文章。比起教书尤其是教授文学,辛格认为做记者对写作更有益。因为一位作家在教授文学之时会习惯于时时刻刻分析文学,而他并不认为分析和创作同时进行会有好结果,“如果他只是偶尔写一篇评论,甚至是写一篇关于批评的论文,这还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时刻进行这种分析,分析变成他每天的口粮,某一天这种分析也会成为他写作的一部分;一个作家,一半是作家,一半是批评家,这非常糟糕。他在为他的主人公写文章,而不是在讲故事。”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有趣的是,辛格在小说中多次提到了意第绪语报纸记者这个职业,也曾将小说主人公塑造成这样一位记者,但对这一职业的描述却没有流露出多少积极的色彩。在小说《思亲小母牛》里,他将主人公的报纸写作工作形容为“靠从杂志上搜罗些奇闻佚事”,写的内容包括“一只海龟能活五百年;哈佛大学教授出版了一本黑猩猩语言词典;哥伦布并不是想找到通往印度的路径,而是想寻找失踪的十个以色列部落”。在另一篇小说《康尼岛的一天》里,他写道,意第绪语报纸编辑对主人公“我”说,“对二百年前的恶魔、幽灵和鬼魂,谁都没有兴趣了……在美国,谁还要看意第绪语文作品呢?我问我自己。”
不止辛格一人对于作家教授文学提出了疑议,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也在《巴黎评论》的访谈里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作家与学者的身份不仅是不能兼容的,且是互相毁灭的,她曾目睹学术生涯如何毁掉她那一代最好的作家。海明威则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既能写作又能教书的自然能两样都能干,好多能干的作家已经证明他们能做到。我做不到,我知道,我佩服那些能做到的。”他自认为做不到的原因与辛格相类似:学术生活会中止外部经验,限制对世界的了解;至于从事新闻业,他认为是没害处的,但如果能够及时跳出还更有好处——他也承认,自己说的这些都是老生常谈。

苏珊·桑塔格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顾自己过往的记者生涯时颇为自豪,比起作家,他相信自己真正的职业是记者,认为写小说和写报道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两者不管信息来源或是才智语言都是一样的。他说自己做记者时一周至少写三篇报道,每天还写两到三篇短评,夜里同事都回去之后他再开始创作小说,“我喜欢莱诺整行铸排机发出的噪音,听起来就像是下雨声。”美国作家E.L.多克托罗做过很长时间的编辑,他认为编辑工作教会他如何把书拆开来再拼回去,教他“学会如何发现自我沉溺状态,为何不需要这种沉溺”,他将编辑对一本书的了解比喻为外科医生对于人体结构的认知,“你对那些东西很熟悉,你可以把它们翻来翻去,还对护士说脏话。”

E.L.多克托罗
美国作家乔伊斯·欧茨在大学担任教师,教授写作课,她对于在大学教书这件事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在接受采访时,她正在跟几个毕业班学生讨论乔伊斯的作品,她表示无法想象还有其他自己更乐意做的事。美国小说家威廉·斯泰伦说,写作课对年轻作者来说可能有推动起步的作用,但更可能“骇人听闻地浪费时间”。对于创意写作课程的问题,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给出了一个不乏讽刺的回答:“在大学教授写作也成就了一些人的个人事业。有一阵子,我很同情他们,觉得他们的东西不可能发表。可事实是,他们挣的钱可能有我一向挣的三倍,这让我不是很理解。”
广告文案、演员与程序员:
成为作家之前
在访谈中,美国作家冯内古特流露出了他对于作家为谋生不得不寻找某个职业现实的憎恶,他曾做过公关和广告人,并认为这样的工作会损害作家的“灵魂”,浪费作家的时间,他将那些不得不从事商业写作的人称为“雇佣文人”。在他看来,这一糟糕状况的源头在于势利的文学生态制度,“由于出版社不再投钱出版处女作,杂志都死掉了,电视也不买年轻自由撰稿人的作品,基金只会补助我这样的老人,年轻作家只能做丢脸的雇佣文人来养活自己。”他说自己已经足够老了,所以不管写什么都直接排印,不管是出版商还是编辑,都完全不会提任何意见。

冯内古特
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也做过文案的工作,然而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文案,“我觉得要正儿八经地为什么轮船螺旋桨啊、啤酒啊、还有航空公司写东西可够难的。我怎么也想不出简短醒目的广告语”,因此他时常担心自己会丢掉工作。但事后回忆起来,他还是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思”,因为在办公室时“人们的举止与他们跟家人在一起时大相径庭”。况且,这份工作的节奏并不过分,“他们给了我一台打字机,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茶”,在上班时,他还曾用公司的机器复印过自己的一部小说。然而比起这个工作,他觉得自己更喜欢做教师,他最喜欢教数学,因为他自己天生对数字不敏感,很同情跟他一样的孩子。
印裔英国移民作家萨尔曼·鲁西迪在成为作家前尝试过做演员,在意识到自己离好演员还差得很远并且经济状况愈发窘迫的时候,他决定去做点别的。听朋友说广告业来钱容易,他去一家广告公司面试了文案工作,但他没有通过创意面试的环节。在访谈中,他回忆起了那一次面试——“假如你遇见一个火星人,他能说英语,但不知道面包是什么,请用一百个单词向他解释如何烤一片面包。”鲁西迪说这个难倒他的面试问题十分愚蠢,“面试者不知道如何在这些人中挑选,于是就不断问一些越来越蠢的问题。最终使人们的工作成为泡影的问题是:月球有多重?”

萨尔曼·鲁西迪
最特立独行的大概要数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了。他在学习农艺学之后成为了一位计算机程序员,对于这份工作,他很快就感到深恶痛绝。然而他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以计算机程序员和他性压抑的朋友作为主角的,在访谈中,他解释自己写作这部小说的原因是:从没见过哪部小说写过进入职场如同进入坟墓。
挣钱分多少,致富有早晚:
作家们的金钱观
诗人是否最好什么都不做而只写诗?T.S.艾略特在访问中回答说,“如果我不需要操心赚钱,把时间全部都花在诗歌上,那很可能会扼杀我的写作生涯。”他认为实践活动对自己很有好处,比如在银行工作或者做出版,都会逼着他在写作时更加集中注意力。“如果一个人没别的事情好做,那么有可能他就会写得太多,导致不能把精力花费在润色一小部分作品上。”

T.S.艾略特
作家如果去从事其他工作,会对文化环境有什么遗憾吗?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答案是:完全不会;如果他照着刚入大学的打算成了一位律师,也不会对美国文化造成什么损失。
那么,赚很多钱对于写作者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海明威曾这样谈论经济与写作的关系,如果钱来得太早并不是好事,必须有很强的个性可以抵抗诱惑,“写作一旦成了你的最大恶习又给你最大的快乐,那只有死亡才能了结。”经济保障当然也有好处的,可以使作者免于忧虑,因为坏身体和忧虑会相互作用。在谈论写作带来的突然致富时,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说,小说的成功肯定改变了生活,但是对她的生活定位而言,并没有什么改变。“挣得更多或者失去金钱,这些前景永远不会影响我的写作方法——我写我的书,如果金钱能随后纷至沓来,那最好不过。”在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略萨则直白地回应说自己不是个有钱人,“假如你拿作家的收入和企业总裁的收入作比较,或者跟别的行业里那些声名显赫的人,譬如秘鲁的斗牛土或顶级运动员的收入作比较,你就会发现,文学还是个薪酬菲薄的行当。 ”

弗朗索瓦兹·萨冈
《巴黎评论》向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提问获得成功和名利是否感到快乐,他有些犹疑地回答道,“我很高兴自己能靠写作维持生计……但我以前默默无闻时,要比现在更快活,快活得多。”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自己经历过一段非常贫困的日子,那时候,为了吃饱肚子,她必须小心在意每一分钱——但她仍然认为自己所经历的贫困并不是真正的贫穷,她成长于钱并不存在的环境中:家住在树林里,自己耕种蔬菜。但是,她觉得钱对于女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你在经济上依赖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想法改变之大会让你自己大吃一惊。”
与以上几位作家给出的回答不同,常年盘踞图书畅销榜、早已赚得盆满钵满的美国作家斯蒂芬金坦诚地说,自己收到的钱已经太多了,不想再收取出版社的巨额预付金(很多出版社急于将预付金支付予他,以此预定他接下来的新作,因为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在出版目录上,就可以帮助出版社集聚人气),“如果纯粹是为了钱,那么我不干,因为钱我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