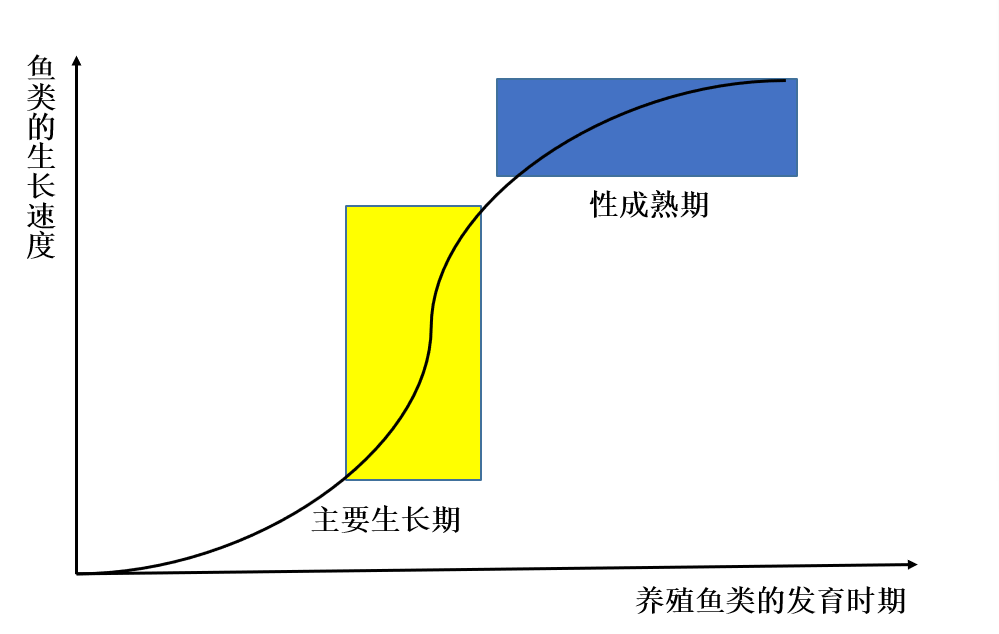第三章元明清时期
第一节剔红与剔犀工艺开始成为了漆香盒制作的主要工艺
元代以来,在宋代形成的文人香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更多的文人雅士参与到香事中来。
香品研制日趋繁多,小型香炉数量明显增多,在香盒的使用品种中主要以陶瓷盒和漆盒为主,其中漆香盒又以剔红与剔犀工艺制作的最受世人推崇,出现了张成、杨茂等雕漆工艺名家。
相较于元代以前,剔红香盒在这一时期之后开始大量出现,人物典故题材的纹样开始出现。
其中被认定为传世品的香盒有:1.大都会博物馆藏黑面剔犀香草纹漆盒;2.大都会博物馆藏朱面剔犀香草纹漆盒;3.大都会博物馆藏剔犀剑环纹香盒。
4.东京博物馆藏剔红牡丹香盒5.安徽省博物馆藏张成造剔犀圆盒;6.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张成造剔犀圆盒;
出土物中可能为香盒的有1.上海博物馆藏剔红东篱采菊图圆盒;2.上海博物馆藏黑漆螺钿人物图圆盒。
元代出土漆盒中未发现带有香料的例子,因此在判断其用途上可能存在许多偏差。其中极有可能是香盒的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剔红东篱采菊图圆。
该盒于1952年上海市青浦县重固镇章堰乡北庙村元代任氏家族墓中出土,是为数不多的元代剔红漆盒出土物之一,对于元代剔红漆器的断代具有标准器的意义。
该盒为元代晚期作品,直径12厘米,高3.9厘米,呈圆形,平盖面,蔗段式,盒内及底部髹黑漆,外髹约三十至四十道枣红色漆,漆色不同于同时代的张成杨茂所制的剔红明艳,相对比较幽暗,漆层厚实,漆质坚硬。
构图疏朗,景物简洁,人物比例较大。该盒的锦文表现方式与张成,杨茂制作的漆器锦文有所区别,相对而言,其雕刻技法比较生硬,人物形象稍许呆板。是元代另一风格的代表,多采用斜刀入画,线条刚直、流畅。
该器整个画面与陶浦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表现的意境非常吻合。有趣的是陶渊明归隐田园,实际生活困苦,想必更是穿不起袍服。
用不起仆童,而这样的形象恰恰反映了后人对于陶渊明题材的诗意想象,这里可能既有对陶渊明生活场景的误解,也有中国文人阶层对于隐者的浪漫想象。
所用材料工艺是最为昂贵耗时耗工的雕漆,而所想要表现的思想却是归园田居的朴素主题。这件器物可能承载着的是现实与想象之间的一种寄托,每当看到这样的画面。
再点起香,便最容易引起使用者的想象,从而暂时脱离现实生活,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任仁发是元代著名水利专家和画家。工于书法,擅画人物、花鸟,尤其精于画马。
从该盒也可以看出其品位与志趣所在。其中以2020年由李经泽及其家族捐赠给青岛市博物馆的“杨茂造”剔犀香盒为例,李经泽称该香盒是16世纪左右的日本当地产物。
从笔者的收集的资料来看,现在日本市面上流传的雕漆香盒中确有大量标注为明代作品的雕漆香盒,且也有多件明显为日本风格的雕漆作品。该剔犀香盒直径10厘米,口径8.9厘米,高3.2厘米。
深刻近底,全器雕刻不作棱角之形,刀法圆润,刚劲有力。堆漆肥厚,形制典雅。器底针刻“杨茂造”款。《格古要论》有载:“元末西塘杨汇,有张成、杨茂剔红最得名”在存世漆器中,发现带有“杨茂造”字样的剔犀器并不多见。
经过对比,两者纹样几乎一模一样,仅有一两处细微区别,漆色层均为18层左右,以红黑黄三色递进分别。漆层总厚度基本一致。
但国内发现的元代剔犀盒所使用的纹样几乎均为如意云纹,与这三件的纹样存在明显区别。倒是与明代的剔犀漆器中常见的纹样非常接近。因此,这类剔犀香盒是否确为日本后来的制作的仿品还是中国元明时期代制作的仍需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张成造剔犀云纹漆盒,直径14.5厘米,高6厘米,盒盖和盒身周缘均雕三组云纹,堆漆肥厚,圆润,光洁照人。
该漆盒漆色总体黝黑,而刀口断面可见朱漆三层,每层相间约2毫米,朱、黑两色漆层相间环绕,整个刀口断面深达1厘米,是一件绝佳的剔犀作品。
更值得一提的是,漆盒底部有针划“张成造”三字款。张成和杨茂同属浙江嘉兴人,故宫博物院也有几件“张成造”剔红、剔犀漆器,为皇家旧藏,与这件漆盒的形制几乎一致。
从元代漆香盒作品中可以看出,主要的工艺类型已经转变为剔红与剔犀。
第二节漆香盒的等级化与规范化不断加强
明代是是继秦汉以后又一个漆器制作大繁荣的黄金时代,明代统治者对漆器十分重视,专门设有御用漆器作坊---果园厂,漆器生产规模也随之扩大。
明代漆器的品种之多、造型之丰富、装饰之繁复,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漆工艺中还出现了一批名匠,如:北京果园厂皇家御用漆器作坊张德刚,擅长雕漆技艺,其父即为元代漆艺名家张成。此外还有江苏扬州江千里、安徽微州黄成。而在香事中,也出现了如朱权、周嘉胄等对香事法度进行系统性梳理的大家。
这段文字非常明确地指出,香盒不仅在质地上有高下之分,色泽、花纹、造型各方面也都很讲究,该文也成为了后世评鉴香盒优劣的重要标准。
明代的香事器具在宋元香事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更为完善的规范体系,其中明代宁献王朱权也起到了较大的影响。朱权为明代洪武皇帝十七子。
博雅好道,多才多艺,文学艺术修养极高,于黄老道学、历史、戏曲、音乐、医卜、茶、香等皆研究精深并著述颇丰。在其所著《耀仙神隐录》中有专门篇章论述香事之道,并且在整理了宋元文人香事器具论述的基础上编制了《焚香七要》以阐述焚香器具之法度。
其中“香盒”条载:“香盒,用剔红蔗段锡胎者以盛黄黑香饼,法制香磁盒用定窑或德窑者以盛芙蓉,万春甜香。倭香合三子五子者用以盛沉速兰香,棋楠等香,外此香撞亦可。
若游行,惟倭撞带之甚佳……香都总匣:嗜香者,不可一日去香。书室中,宜制提匣,作三撞式,用锁钥启闭,内藏诸品香物,更设磁盒磁罐、铜盒、漆匣、木匣,随宜置香,分布于都总管领,以便取用。须造子口紧密,勿令香泄为佳。俾总管司香出入紧密,随遇燕炉,甚惬心赏。
朱权的《焚香七要》对明清两代文人香事影响极大,明代后期高濂《遵生八笺》、项元沐《蕉窗九录》、文震亨《长物志》、屠隆《考梨余事》等皆有转录阐发,并且传至东亚各国,日本享保十八年(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杳熏堂的《香志》亦摘录了朱权的《焚香七要》。
明代剔红漆盒以花卉图案为多,而此漆盒则一面人物,一面花卉,较为少见。尤其此盒堆朱不厚,而镂刻层次颇多,刀法属于藏锋圆润一类。
明成化、弘治年间,中亚蒙古可汗先后进献狮子数头。随之,中亚一带的乐伎舞人也不断涌入中原,使代表着异国风情的狮子舞,盛行一时,胡人戏狮图即产生于此社会背景之下。
从造型尺寸上来看,亦极有可能是当作香盒使用。金属胎薄且不易变形,髹涂上百遍漆后,也不会显得过于厚重。其中锡具有较好的延伸性,质地轻,制作器物更为简便,且相比较金银胎,锡的价格更加低廉。
而做为香盒使用,锡质胎也具备足够的稳定性,对于保存香料更是尤其独特优点。
明代收藏家周嘉胄著书《香乘》,对于香药的名品以及各种香疗方法的描述一应俱全,是中国香文化集大成的经典之作。其中香的储存方法中就有写到用锡质盒子对于香品保存的优点:“倘得真奇蓝香者,必须慎护。
如做扇坠、念珠等用,遇燥风霉湿时不可出。出数日便藏,防耗香气。藏法:用锡匣内实以本体香末,匣外再套一匣,置少蜜,以蜜滋末,以末养香。
香匣方则蜜匣圆,蜜匣圆则香匣方。香匣不用盖,蜜匣以盖。总之斯得藏香三味矣。”锡质的盒子,内放奇蓝本物的粉末,用蜂蜜将其浸透,置于奇蓝香旁边,以此养香。
现在仍在有人使用这种方法来保护奇蓝香,可以保其香气不散,质地湿润柔软不致坚硬。
从目前发现疑似为漆香盒种类看,有剔黑、剔红、剔彩、螺钿、戗金、素髹、彩漆、描金等,但从明代出土物中仅发现一例盒内存放有香料作为直接证据的漆盒,即楚昭王墓出土的一件朱漆素髹香盒。
外还可能用作香盒的有:1.上海闵行马桥仁济道院顾守清墓出土的明永乐款剔红牡丹纹雕漆盒;2.浙江南浔聚星塔出土的红缠枝牡丹纹雕漆盒;3.常熟练塘公社石泉大队杨家坟出土朱面剔犀漆盒一对;
上海闵行行马桥仁济道院顾守清墓出土了两件明永乐款剔红牡丹纹雕漆圆盒盒为旋木胎,盒底带一圈足,蒸饼式。口径5.6厘米、高3厘米,扁圆形,盖隆起,盒盖中央雕刻牡丹一朵,四周枝叶舒展,漆层较厚。
剔刻痕迹较为斑驳,纹样顶面及边缘过渡非常圆润,有很明显使用痕迹。盒内与底部髹黑漆,左侧针刻"大明永乐年制”。墓主顾守清,明代仁济道院院主,卒于嘉靖丙成年(1526年)。
浙江南浔聚星塔明万历年间创建基底石函中出土了一件剔红缠枝牡丹纹盒,口径10.5、高4厘米,圆形,盖面深雕缠枝牡丹三朵,花苞枝叶相连,图案非常丰满,内里、盒底髹黑漆,底左侧针刻“大明永乐年制”。
这三件剔红圆盒,分别出土于塔基和道院主的墓葬中,为佛、道两教供奉之物,因此极有可能为盛放香料之用。明代开始,在佛、道两教的影响下香具开始以陈设的形式进行展示。
如山西省博物馆收藏的《金绘衹园大会卷》中描绘的一幕,长卷中后部分,画面中众僧围绕在一组香具之前,其中包括三足香炉、直筒香筯瓶、瓶内置香匙与香筯、五重舍利塔、圆形香盒形成一组陈列的画面。
此后,以炉瓶三事的香具组合陈设也逐渐成为了皇室官家庙堂礼仪之器,并以此形成了中国传统香事中最为正统的焚香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