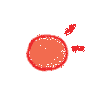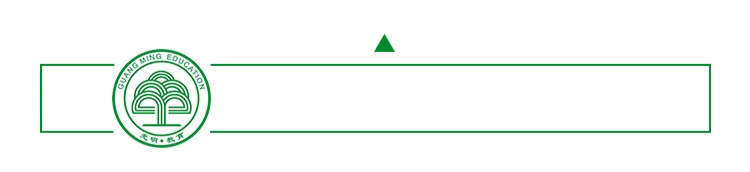森之园的孩子们在摆弄着玩具模型。这天有霾,他们没出门活动(李伟 摄)
记者/黄子懿 实习记者/王亮
一次腾退
2018年冬至日的北京昌平七里渠农场,在阴云中的远山、高耸的枯树、冰封的河水映衬下,空旷而萧瑟。一阵欢声笑语打破了寂静,院子里蜂拥而出上百个孩子,有的踩着树上护具,一步一步往上爬着,偶尔失足摔跤也不喊疼,站起来笑着继续爬。原来这个占地330亩的农场里除了有成片的桑树、杏树、苹果树、散养的鸡狗,还有一个幼儿园,这会儿正是幼儿园的自由活动时间。
七里渠农场原本更热闹。最多的时候,这里共存着近10所幼儿教育机构,六七百个孩子在里面嬉戏打闹。但由于农场土地性质的原因,农业用地不允许开设教育机构,农场内的园子和机构们已在近一月之内先后搬走,只剩唯一一家紫水晶蒙养幼儿园。紫水晶在农场有两个院子,房间门上已被红漆喷上了待腾退的数字。一到下课,就有好奇的孩子们围在这些房屋周围,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这些数字的含义。
“完全不知该怎么办了。”家住回龙观的鲁筱英最近焦头烂额。她4岁的女儿在其中刚刚就读不过半年,却面临着搬迁难题。女儿入园前,她考察了多所幼儿园最后才选定了紫水晶。为此,她把家从北京南城搬到了回龙观,还换了一份工作。
常人或许很难理解鲁筱英的决定。从外表看,紫水晶质朴得甚至有些简陋。园内墙壁已发黄,也没操场和体育用具,只有一处木头爬梯,园外是一片果园。特别之处在于,紫水晶是一座森林幼儿园,在七里渠农场已有10余年之久。与传统教学方式不同,这里倡导解放天性、亲近自然,混龄组班的孩子们可以露营、打滚、摘果子、玩泥巴、喂母鸡粮食……每年,还有定期的“童子军”远征。孩子们会脱离大人几天几夜,跟老师远足并在外过夜,回来后一头草灰、满身泥土也开心无比。用一位家长的话说,这里“没有衣冠整洁的洋娃娃,孩子们都像野生的,浑身脏兮兮”。
盖娅的孩子们在昌平的农园大棚内作画。按照要求,他们将把南瓜从种下到成熟、再到进入人类之口的过程画下来
这是一座森林幼儿园,在农场已有近10年之久,不仅在回龙观周边小有名气,更有诸如鲁筱英等家长跨越大半个北京城来投奔。森林幼儿园于20世纪50年代发源于北欧,后传德国、日本等地。在这类幼儿园中,森林是教室,自然是老师,孩子们或席地而坐,或满山蹿跳,学习多靠游玩,享有绝对主动权。在城市钢筋水泥外,孩子们在广阔的森林自然中,有更多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最近10年来,森林幼儿园也在中国落地,分完全式、混合式、定期式、阶段式等不同模式。由于倡导自然教育,他们多位于城市郊区,距核心区较远。仅在七里渠农场,就曾聚集了紫水晶、自然学堂、乐知学堂、源起自闭症儿童关爱中心等教育机构,不同园子的孩子在此嬉戏互动、好不热闹。
腾退令下达的当晚,这些机构就连夜搬出,或直接停课,或借用在他校教室暂避。紫水晶由于规模较大,被暂时保留了下来。400多个孩子不知未来何从,一些家长开始频繁在网上呼吁、给市长信箱写信,希望在此地保留紫水晶。
“如果按照现行规定,森林幼儿园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所有森林果园都只存在于农用地、林地或公园用地中,而这些用地都是不让办幼儿园的。”一个看过该区域规划图的规划师家长说,目前只有城市教育用地或商业用地允许办园。“很无奈,孩子们被用地规划困在了钢筋水泥里,自然和童年被分割成了泾渭分明的区块。”
与紫水晶的全日制不同,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旗下的盖娅自然学校也成立了盖娅森林幼儿园(以下简称“盖娅”),但没有固定场地,采用定期活动式——很大程度上也有土地的原因。盖娅拥有两所农园,分别位于平谷和昌平,用地性质都不被允许申办全日制幼儿园。盖娅因此分为小、中、大班,一年分班举行10次活动,地点和主题也各异。
2018年12月22日,盖娅组织了十几户家庭乘坐大巴到达昌平郊外的农园。马兰是园长,她为当日活动定下的主题是“包饺子”,其中有南瓜馅儿——这是一年以来,他们教孩子观察南瓜从发芽到成熟的最后一步。这是大班今年的最后一次活动,有11个孩子将从此“毕业”。
“春天我们种了南瓜种,然后施肥、保水、除草,用两次课收获,再观察什么动物会吃这些农作物。这次把南瓜吃掉,孩子们就能建立完整认识。”马兰是盖娅的园长,她和同事设计了这个课程。她要求孩子们把整个过程画下来,并饭后讲解。一个4岁的孩子看着大人们包饺子用的不锈钢厨具,不知如何表达,就画了一口锅,写上了“不xiù gāng”。
盖娅的孩子们在室内等着吃大人们包的饺子(李伟 摄)
为何选择让孩子们上森林幼儿园?对许多家长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周边现有幼儿园的不满意。2016年女儿2岁时,鲁筱英就在丰台区周边看幼儿园。没有北京户口,能供她选择的多为私立。小区内有一个幼儿园,她从窗户就能望见园内,有塑胶跑道、有塑料滑梯。但鲁筱英看到孩子们每天上午来,下午被家长接走,“几乎不会出来活动”。而就这所幼儿园还人满为患,她没报上。
被朋友引荐去到紫水晶参观后,鲁筱英被农场环境吸引了。她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书里,海伦·凯勒讲述自己7岁失明后,家中为她请了一位老师,老师教她语言,带她活动。一次,老师在她手心写下“water”(水)这个单词,但她总把“杯”和“水”搞混。泄气时,还把老师给她的瓷娃娃摔坏了。
老师见此,带海伦·凯勒走进水房,将她的小手放在水管下,让清凉的水滴在手心、流过手掌,后在她的手心画了几次“water”。“不知怎的,语言的秘密突然被揭开了,我终于知道水就是流过我手心的一种液体。”海伦·凯勒写道。从此,她再未忘记这个单词,也像开窍一般,迈向了作家的路。“孩子们需要这体验,得接触自然才能吸收。光跟他讲这个热那个冷,没有体验他是不会懂的。”鲁筱英说。所以她当初坚定地搬家,将孩子送到这里,没想到刚就读半年,紫水晶幼儿园就要腾退了。“孩子们与这儿的一草一木,一秋千一滑梯,早成为一体。现在转园也不现实。”
盖娅森林幼儿园园长马兰(李伟 摄)
“看见孩子”
2017年,家住北边的李云岭因工作调动搬到南城。搬家后,他一路“地毯式”搜索,看了10多家幼儿园,才找到一家符合自己标准的幼儿园,对方是秉承森林教育理念的机构。从事文化出版业多年的李云岭说,回想自己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工厂化的教育,他不希望女儿再接受模式化教育。
最初选园时,李云岭曾探访过某著名连锁幼儿园,设施特别豪华,但同事孩子在里面,说老师不许孩子上课随便走动,“有了课程纪律的概念”。另外,很多幼儿园老师流动性大,待遇一般,无法保证全心全意。“很多大幼儿园KPI一压,家长一压,老师就要维持秩序,天天就拍些照发家长群里。”李云岭说,“这样孩子灵性会变差。”
李云岭最终选择的是位于北京南城的“森之园”。森之园离家较远,车程有半小时,但不远就是一个占地上万平方米的大公园。2018年12月21日,有雾霾,20多个孩子没出门,都在室内活动。整个上午,他们在屋内喧哗玩耍,声音不止,仿佛想要发泄出那股没在室外消耗的精力。负责人张静说:“只要不是雾霾,都会去户外活动。”
为何很多家长和教育者认为,森林自然教育很重要?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有研究表明,经过森林教育的孩子除了体能佳、体格好、动手能力强外,在合作意识、环保意识和抗挫折能力都比其他同龄人更有优势。森林教育中的孩子也多“放养”,没有太多固定的课程和计划。
2016年,曾从事儿童博物馆工作的张静决定创办森之园。直接原因是,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找遍全北京,同样也没找到符合自己标准的幼儿园。此后,张静在盖娅做过半年志愿者,也曾设计体系课程,最后还是根据情况放弃了。她相信孩子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并定下规则:每次户外森林活动,都由孩子们自己去商量去哪里玩、如何玩。他们可以听蝉鸣蛙鼓,占丘为王,也能看银杏归根,品冬夏凉热。
幼儿园其中一个主要特色是:没有课程表,也没有“课程”,老师是观察者和陪伴者。“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就是从森林来的。”入园之前,张静会跟家长面谈,说清楚老师不帮穿衣服,也不喂饭,以寻求理念相近的家庭。在她看来,“自然”有两个含义,一个名词,一个副词。
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于其中认识万物,也能体验到生命规律。入园后,李云岭去接女儿,女儿不是捧一把树枝,就是捡一堆石头带回家。一次,李云岭和同事带孩子去天坛公园,秋天的天坛很多树木和落叶,两个森之园的孩子对这些表现出很大兴趣,一起研究观察树叶形状,透过残叶缝隙看阳光。另一个孩子起初还一起玩,但很快就表现出倦怠,不停地找妈妈。“可能是想得到关注和保护。”李云岭说。
进入紫水晶后,鲁筱英也感到了孩子在变。一次,她跟孩子走在路边,孩子突然蹲下,看着路边一朵小花,鲁筱英下意识制止。孩子说:“妈妈,我不会摘它的,我只是想看看是什么花。”冬天来了,孩子还会从家里带小米到农场喂食小鸟,农场很多果树都系上了投食盒。“她好像真的懂得了一些对生命的感悟和感恩,这些东西都是在教学中领悟的。”鲁筱英说。
森之园森林幼儿教育机构负责人张静(李伟 摄)
对大自然,儿童也有着极好的适应。森之园的公园里有长约2米的45度小石坡,是孩子最爱去的地方之一。张静观察到,一个3岁小女孩刚入学时天天坐在坡顶望眼欲穿。第一周,她颤颤地盯着土坡,双手抱膝,不敢往下;第二周,她看着对旁边爬滚的同学非羡慕,想鼓足勇气而下,但仍犹豫不决;第三周一天,女孩终鼓勇气,屏住呼吸,闭住眼睛,风一般直冲而下。之后,是不能抑制的兴奋和狂喜。
“不用担心孩子们危险,他们很多时候自己会规避危险。”马兰说。盖娅活动也有一座6米多长的山坡需要征服。与森之园不同,盖娅的定期活动都有家长参与,态度各异。最初,有家长看到土坡非常气愤,“你们怎么能让我孩子玩这个?”马兰拗不过,让步让家长一上一下搭帮手,结果孩子们几乎是他们手把手递下的。
后来,马兰学会将家长和孩子分开活动。待孩子们要下坡,她就让家长往山坡看。“你们看看孩子们能否自己下这坡?”马兰对家长们说,“他们不仅能下,而且我告诉你们,他们后面下的姿势,肯定和第一次不一样。”果然,孩子们起初都是连爬带滚,到后面就能迈着双腿冲下了,就这样一步步适应。
“家长都经历过这个过程。”盖娅活动中的家长牙格达说这话时,7岁儿子正在室外一处水塘玩耍——与枯燥的包饺子相比,结冰的水塘显然更有吸引力。近10个孩子围在水塘边,用脚跺、用树枝戳,把约5平方米大的冰块搓成若干块大小不一的冰,用双手浸入冰水捧起,拿着挨个观察。室外的儿子拿了一块冰,试着用屁股坐上去感受,凉得受不了,马上站了起来。
牙格达说,这水塘对她儿子并不陌生。曾有一次,儿子大冬天掉进了这个深过半米的水塘,水面直逼脖颈。其父跳下去捞了上来,打湿了全身和手机。而这天活动,有个4岁孩子也不小心掉下去了。父亲看着湿漉漉的他笑了笑说:“我小时候可比你这掉得更深。”
“家长的变化其实比孩子更大。”马兰一边指屋内的家长,一边指着嬉戏水塘的小孩说,如今孩子们在外玩耍,家长不再焦虑地不时出来望了。近0℃的室外,唯一围着孩子转悠的父亲,是因平时不常来,主要母亲带。“看着有点紧张,要盯着孩子。”马兰望着这位父亲说,很多家长刚来时,只要孩子奔河边稍微走走,家长就立马叫停。
张静把这个转变称作家长“看见孩子”的过程——这并不容易,很多老师也无法做到。曾经,园子里外采活动时来过一位学历高的老师。活动结束,这位老师带着孩子们集合,对着小朋友们说:“孩子们真棒,你们今天表现得很好!”
张静问记者:“你觉得这话有什么问题?”记者想了会儿,说:“表现得好坏不应拿来评判的?”张静继续说:“问题是‘表现’,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活动,不是‘表现’。我们凭什么认为那是‘表现’给我们的?‘表现’两个字,体现出老师把自己和孩子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张静承认,这可能有点抠字眼,但她希望老师、父母和孩子是平等相待的。
森林幼儿园是一个小社会,而儿童世界则是成人社会的雏形。一次,森之园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在公园设置了监狱。这个并不新鲜的游戏,孩子们衍生出了合作、解救、策反。警察把小偷抓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于是,警察会想办法把小偷放出去。一次一位警察刚刚教育完一名小偷后,另一名警察悄悄来说“你给我金子,我就把你放出去。”张静听了难以置信。“一个4岁的孩子,竟然懂得索贿了。”
园里对“打架”也持开放态度。张静将其视为孩子们社交学习的机会。“幼儿园阶段是没有霸凌的。”不久,森之园转来一个男孩,或许是由于初来乍到,他刚来时展现了很大“破坏力”,被小朋友称为“雷克拉”,源于孩子们喜欢的一本书《雷克拉毁了它》,讲述的是一个毁掉别人积木的小恐龙的故事。“雷克拉”做的事和书里一样。
一日在小水池旁边,一个4岁的女孩安静地玩着水,女孩入园时害羞胆小,有小朋友说话大声了都会被吓哭。“雷克拉”走近水池,蹲在女孩旁边,突然对着女孩撩起水,弄湿她一头。但女孩并未惊慌生气,她用手抹一把脸,看着“雷克拉”说:“你是想和我一起玩儿吗?”“雷克拉”惊愕间点了点头,两人玩起了倒水游戏。
室外结冰的水塘更能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他们后来齐心把这块冰弄碎了观察、玩耍(李伟 摄)
自然的疗愈
森林幼儿园中的自然教育,也正被应用到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身上。比如,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们。
从七里渠农场搬离后,源起自闭症儿童关爱中心在离昌平城区40分钟车程的郊外,找到了暂歇处。2018年12月20日,十几位源起的自闭症孩子,站在智光特殊教育学校的大厅内,与来自拉美大使馆的数位外宾联欢。这些年龄跨度3~13岁的孩子们表演了吹笛、唱歌、朗诵,他们口型整齐、吐词清晰,远看与常人无异。
但在台下,一位10岁左右的少年不时放声大叫,进而哭泣。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少年癫痫发作。周围老师立马将他扶住,把他唤醒。“自闭症的孩子对环境极度敏感,他们不适应这个人多的新场合,会有各种反应。”老师如荟说。
如荟是源起的创始人和老师之一。几年前接触到自然教育理念后,她的团队将此理念和方法运用到自闭症的关爱和教育上。2016年,源起成立,在七里渠农场建立疗愈基地,与紫水晶为邻。一栋3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与农场的330亩土地,成了数十位自闭症儿童的疗愈乐园。孩子们在此种地、爬树、磨豆腐、喂食动物等。
一般来讲,自闭症的孩子敏感、紧张,并极易放大情绪,难保持长时间专注。从这次表演效果看,进步显著。表演前,如荟刚给他们上完一节一小时的正常课程,秩序正常。而过去课程一度是15分钟一节。“你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就大叫了、就大哭了。”如荟说。
进步最明显的一个孩子今年13岁,名叫正宇,四年前送来,是中心最大的孩子。如荟至今都记得,正宇被送来的场景:一个9岁的男孩像一只猴子那样趴缠在父亲身后,因为紧张,他小心翼翼地探头观察,不断抓捏着父亲的脸,父亲无可奈何。母亲的脸曾经被抓烂,她一度将头发剪短,免得被抓秃。
交谈后如荟得知,正宇家庭条件较好,父母曾辗转于广东、江苏等地的特殊学校求助,但孩子待不住,大闹过课堂。对于传统的特殊教育课堂,如荟很熟悉。她曾是北京某所公立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见过了里面诸多“训练式”的教法,她觉得不对路。
在那里,部分特殊孩子课业压力也很大,有的也要正常参加高考。教室内一天要上九节课,一节课45分钟。如荟认为,这种方式明显不符合特殊孩子的需求,“却是符合家长的内心期望的”。
如荟因此会问家长:“你们把孩子送过来是有什么期望吗?”很多父母说,希望儿女能快乐。如荟一听,说:“你们再回去好好想想吧。”家长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实话:“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有进步的。”
进步谈何容易。正宇有严重强迫症,父母列了一个清单:不能吃炒饭和饺子。每次吃这两种食物,正宇都把青菜、肉、饺子皮等挑出来挨着分好,才吃下去。还有很多次,课程临时有调,正宇不能接受,直接躺在地上,谁叫唤也不起来。刚接触时,他至少有三次,在两秒钟内,用手猛然将如荟的头朝下往地上按。
转变始于自然。为了疗愈,正宇的父母从南方搬到北京,在中心附近租了一个农家院,过上了农村生活。如荟让父母在院子内弄了一个沙坑和一个泥坑,这后来成了正宇最爱的地方,经常在家滚得一身沙泥。而用餐时,如荟也会故意安排饺子和炒饭,也不强迫,任正宇摆弄着饺子和炒饭,一顿饭能吃上四小时。久而久之,正宇感到时间的流逝,逐渐改掉了习惯。
“得给他一个自然的环境,在这环境里,大家的状态是松弛的。”如荟说,中心该基地曾辗转多地,搬过小区、租过别墅,但都没农场的自然环境好。“孩子有时控制不了情绪,需要一个大场地去释放。”在农场,孩子们每天早上到达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绕场去跑步40多分钟,然后回来上课,进而是20分钟户外活动。土坡、沙坑和果树,仍是孩子们最爱的地方。
北京一家知名小学曾在中心做过联谊活动,要使用铁锹锄地,给菜地扎上栅栏。这家小学的孩子来了很兴奋,但又不会用铁锹,一个孩子很快手就破了,于是哭着叫着妈妈。“哟,这还得了。”爸妈一看,赶紧给大家买了100副手套。“许多城里孩子现在没这样的机会了。”如荟感慨着。
2018年,看着孩子们越来越大了、行为也趋向正常,如荟试着带他们出门游学,先是苏州,然后安徽、西安。许多自闭症孩子有脾胃、肝脏问题,身体更敏感。呕吐、腹泻是常态。小琦就是其中一位,但一次西安游学后,家人发现孩子腹泻减轻了。原来,他更适应吃面食。
“孩子比以前好点了。”小琦母亲说,自家孩子的情况属中等偏下,但她能感到进步。过往,如荟让她家晚上8点半必须上床睡觉。“不可能。”她当时答道。孩子入睡特别困难,有次半夜12点还没睡着,因此情绪失控。而几次完全脱离父母的游学后,孩子变了。如今很多个夜晚,过了8点半,当她忙完会发现,孩子能自己更衣独立入睡了。
何去何从?
盖娅大班的这后半年活动中,孩子已上小学。马兰明显能感到,家长们的新一轮焦虑来了。一次活动,马兰通知家长们带上两个本子。很多家长一听后就问:“应该买什么本子?多大的?厚度多少?什么颜色的?需要有线格子吗?”
森林教育并非万能的,甚至是有短板的。倡导回归自然的理念下,家长们也有担忧:在应试主导教育体制下,习惯了在接近原生态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会不适应,甚至掉队。孩子在园内的最后一年时,紫水晶会成立一个毕业班,准备毕业和幼小衔接。一位家长说,升至毕业班时,孩子有时会流失2~3个。
园方每年会组织一个说明会,邀请已升学的家庭回来座谈,分享经验。至少,受邀回来的很多孩子和家长,都顺利完成了转变,不乏在名校就读并成绩优秀者。“很多毕业家长说,最多1~2月他们就能适应了,而且比别的小孩思维更活跃。”前述家长说。
焦虑并非只是家长的,更有教育者的。2018年,森之园开办第三年,包括她自己儿子在内的很多孩子即将升学,张静曾有过自我怀疑,这种教育方法究竟是否合适国内环境。纠结下,她选择去日本的森林幼儿园考察。“我想去看看,什么都不教的孩子上学后究竟是什么样。”张静说。
日本森林幼儿园的发展让张静感慨。他们历史沉淀更久,也更“自然”,有些甚至没实体教室,以天为顶,以草做地板。如果下雨,就找一个亭子听雨。日本教育者们告诉张静,多数孩子升学并未表现出太大不适应,甚至后劲更足,这让张静明朗了起来。“我们要相信森林教育带给孩子们的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能力。”她说。
“现在国内做的,还都只是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马兰也去过日本考察,她这样评价国内目标的发展阶段。除了模式多元外,日本还更加注重本土意识。一所富士山下的幼儿园,会围绕着富士山做三年活动,探洞护林,在培养孩子体魄和性格的同时,也培养其本土和环保意识。
马兰的下一步计划,还是想把盖娅做成全日制幼儿园,以更好地践行理念——目前看来仍遥遥无期,土地仍是最大的困扰,这是当下所有森林幼儿园都面临的难题。在寸土寸金的超大城市,严格的规划和昂贵的土地,暂时不允许森林幼儿园如雨后春笋般生根发芽。
前述从事城市规划行业的紫水晶家长透露,根据规划图,七里渠农场腾退后可能会用作公园绿地使用,“反正不是农地了,是城市建设用地”。而这,也正是一些森林幼儿园应对土地问题的方案,即依托公园而生。盖娅在初班时多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活动,森之园则直接开在公园附近,孩子过一条马路,就能去畅游。
采访中唯一曾解决土地难题的,是一家门头沟区森林幼儿园,租用了当地乡村小学的曾用地。但也因规划原因,这块土地被征用,幼儿园刚搬了家。负责人因暂未安定婉拒了采访。他说,在成都和广州有顺利办学者,花高价拿下一块性质符合规划的土地,将其打造成森林的模样。由于成本高,这类学校普遍走贵族路线,每年学费高达20万元。
无论森林幼儿园未来何去何从,孩子们的未来终究是要融入社会的。对于未来,父母们的选择与其他家长无异。有北京户口、具备条件的,多选择公办小学;外地户口的,准备公办的同时,也在为上私立小学做准备。
李云岭说,他将优先考虑公办小学。“她迟早是要融入这个社会的。”李云岭指着下园内的一个玩具帐篷说,“不可能永远保护她,像这个小房子一样。永远待在这里,你会看不到别人。”他最希望孩子学到两样东西:第一是如何做选择;第二如何跟人协作,而多数的协作必须在整个社会大环境里方可完成。
对源起的自闭症孩子,家长们也有自己的思考。正宇的母亲,最近不再接送孩子了。家里租用的农院距离校车站点不远,她开始训练儿子独自坐公交车往返,目前已有一月有余。自闭症鲜有完全治愈的可能,但她希望儿子具备基本的自理能力。“如果不搬家,正宇以后说不定能做农场的一个园艺师。”如荟说。
而对于森林自然教育的功效,家长和教育者也表达了自己的审慎。李云岭说,孩子原本就在一直进步,这是他们的天性,在茁壮成长完成对世界无尽的好奇和探索。“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也不可假设的。”张静说,“很难说,在不在森林教育中长大,孩子们会有什么不同。”
盖娅活动这天,马兰为每位小朋友发了毕业奖章。他们拿着奖章,争相给爸妈展示,笑颜绽放。颁奖结束后,需要全体合影。马兰问了一句:“咱们是在室内还是外面合影啊?”孩子们齐声答道:“外面!”
(文中如荟、家长和子女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