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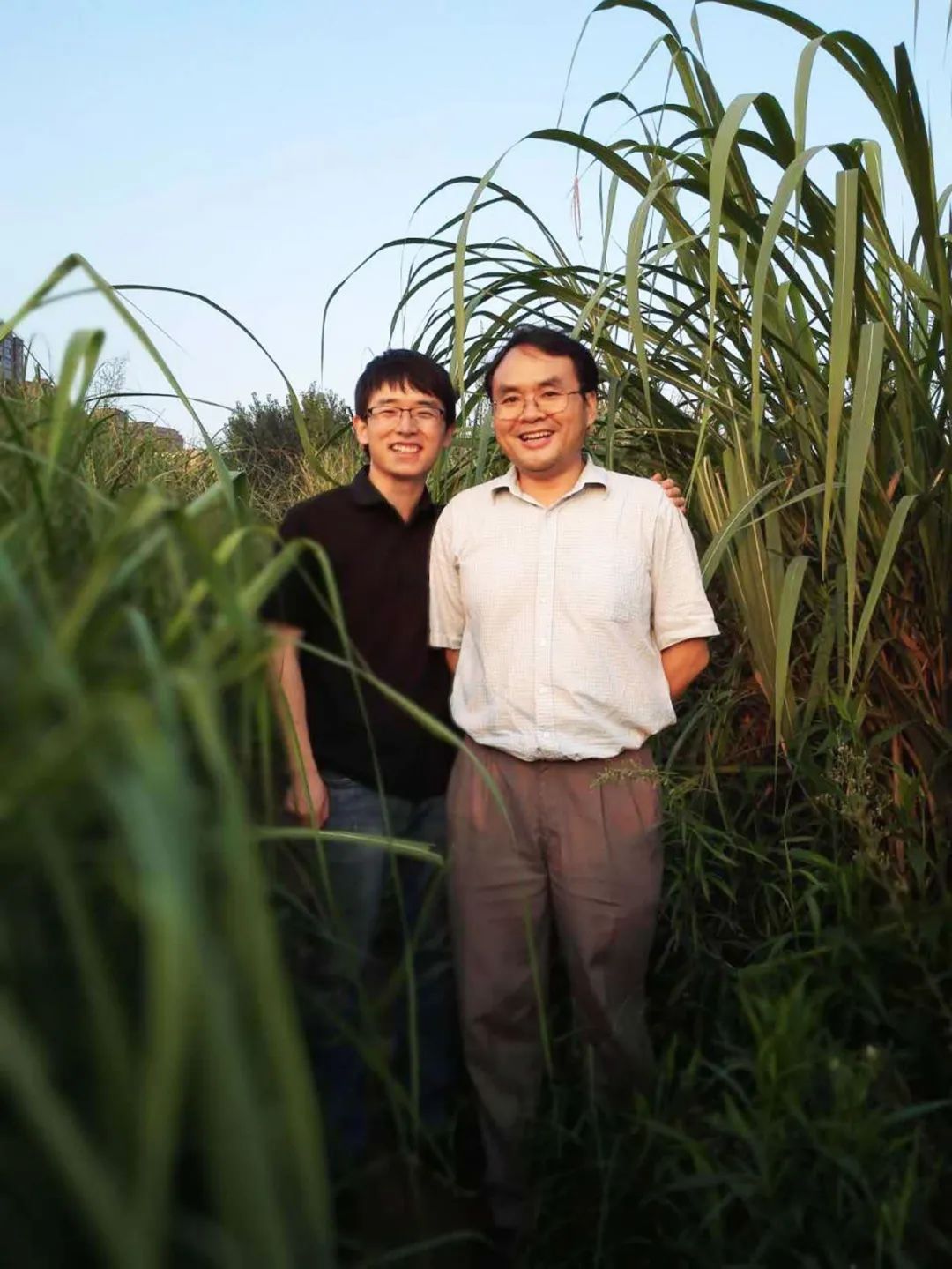
程猛和导师康永久教授
“你的童年是怎样的?”
“童年是和小伙伴在村口弹弹珠、丢沙包、折纸飞机,是爸爸开着拖拉机拉着很沉的铁碾子在村里的打谷场上一圈圈打转,是放学坐在妈妈的自行车上看着街边的烙饼馋哭……”
1989年,程猛出生在安徽三县交界的一个村庄,母亲是邻村村小的民办教师,父亲是农民,打理着十几亩地。凭借着每逢大考就超常发挥的运气,他一路升入区县的重点中学和市里的重点高中,16岁就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
在回忆里,他小学的时候成绩就是前几名,算得上是村里人口中的“读书的料”,和童年的伙伴一起沿着教育阶梯向上走,同行者却越来越少。
回顾成长,他却觉得自己充满侥幸,许多极有天资的小伙伴因为某次大考差了几分,或者遭遇了学业阶段转换过程中的不适应,或者家庭出现某些变故,走着走着就变换了人生道路。有的人在读书这条道路之外绽放了自己的才华,有的人正困于现实的逼仄。只有少数人,通过高考突破了命运的瓶颈。

母亲和程猛
2015年,程猛第一次和博士生导师康永久教授谈起了自己对农家子弟的研究兴趣,康老师突然说了一句,“我觉得你内在还有对农村出身的焦虑。”
这让他心一震,也触动自己去认真思索: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们究竟是如何面对自己的农村背景的?他们又是如何“自己将自己”创造成了一个读书的料,从而走上了一条走出农村、子不承父业的人生道路?这一旅程中的郁结和疏离又要如何才能看见、如何得到安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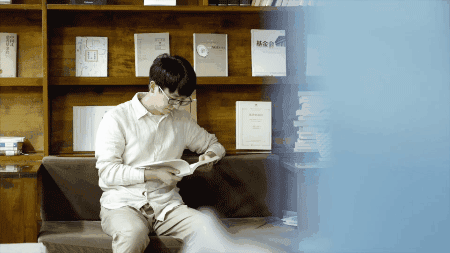
程猛在北京常青图书馆,翻阅自己的研究
做这项研究并不容易。因为那些他想要探索的问题经常勾连的并不是诗情画意的回忆,像是“家境的限制”“对农村背景的理解”“和父母的关系”等等。
研究过程中,他还选择用自己的勇气和真心去交换,把自己1万多字的自传发给愿意接受自传写作邀请的寒门学霸。
截至目前,他已经收集了52位农家子弟的自传,访谈进行了36位,总计130多万字。自传传主多数出生在1980年到1995年之间,正在985、211高校就读或已走出校园。相比于许多没有走读书这条路的小伙伴,高等教育让他们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发展空间,也积压了忧愁与困惑,关于童年、家庭、事业、婚恋……
以下是程猛的自述。

程猛讲述自己的故事
故事的开始
“每个人都是一口深渊,我们俯身看去的时候都会禁不住头晕目眩。”一个学生的自传,开头写了这么一句话。
我学习的教育学,是一门迷恋成长的学问。每当我读一篇自传,就如同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之渊,随着时间之流飘荡,一次次被打动,时悲时喜。

图片来源网络
在收集和整理自传的过程中,会发现农家子弟都拥有同一个“走出去”的梦想。
小安出生在丘陵地区,家附近都是煤矿,煤矿里除了灰色的房屋、街道,就是山。她仍然记得小时候老师问她的梦想,她想都没想就回答:“我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但我知道它在我家窗前那座山的后面。”
云明已经博士毕业。他出生在山东,从小就被灌输:高考是最公平的出路。高中几年,有时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完全出于自觉,也不需要老师来督促,因为没有退路了。

摄影师刘飞越作品
向上发展、走出村庄、出人头地,靠读书改变命运——他们的梦想宏大而目标模糊,很少会想究竟走到哪里才可以停歇。
而城市学子的梦想往往更精细而具象。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出生在城市的溪莹从小就拥有了比较惬意的生活和更多尝试的机会,“当时参加了许多兴趣培训班,有舞蹈、水彩画、素描、电子琴、小记者等。不过只有小记者班坚持了下来,成为一段难忘的经历。”家境优渥的孩子不需要去对抗命运,有更多追求个人发展、探索人生可能性的空间。

图片来源网络
家庭
农村家庭常常对能读书的孩子报有 “出人头地”的盼望;但同时,整个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弱,在孩子学业或其他方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该如何提供适切的帮助。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进入市里的重点高中以后,成绩从入学时的20多名一路跌到班里很后面的位置,主因是物理和数学,当时觉得自己怎么学都学不会,而别人看起来怎么就毫不费力。
那段时间,我选择了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每周六晚上都会去以前初中学校旁边的网吧“包夜”,几块钱就可以在网吧待一夜。沉浸在坦克大兵的游戏世界里,就可以短暂地忘记那些无可倾诉的烦忧。带着对父母的负疚感,晚上经常只吃方便面。
记得当时一连去了好几个星期,第二天一早回到家就倒头大睡,慢慢我妈就发现我不太对劲。有一天醒来后,她倚在堂屋正门的门框那,问我:你到底在干吗?我看着她红红的眼眶,只好坦白。那个时候我妈妈哭了,她没有批评我,就是在那里哭,我也哭得很伤心。
后来,我就没怎么再去过网吧。这一场哭泣重新把我拉入学业轨道,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吧。

图片来源网络
钱
“钱”在自传里经常被提到。在那时搜集的自传中,32位中上阶层子弟一共提到过44次钱,而23位农家子弟却提到了92次。
浸润于贫寒的生活境遇,农家子弟从小就非常清楚父母能付得起什么,付不起什么,常常提到的是“没钱”“要钱”“攒钱““不可能有钱”“借钱”。
在城里长大的小文,小时候父亲慷慨地每月给她生活费,当得知她分文未动后,感叹:“财商教育到底是没成功——只会存钱,不会花钱!”这是家境优渥给予她的特别记忆。
河源却没办法如此潇洒,与钱关联的家庭记忆与小文是截然不同的,“全家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爸爸送液化石油气挣的1000多元/月,爸爸的工作很辛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节假日,总是骑着自行车,带着七八十斤重的煤气罐奔波,楼上楼下地搬运,每瓶才赚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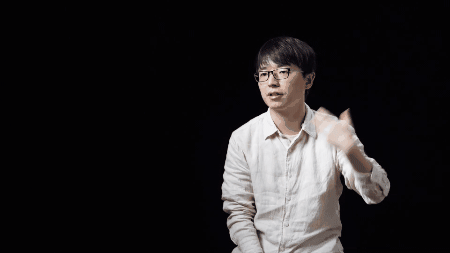
程猛讲述“背煤气罐”
2块钱,就这样很具体地和父亲的辛苦劳作紧紧相连。这样的孩子会非常清晰地记得那是“三毛钱的麻花“ “五块钱的试卷”。因为钱对他们来说太稀缺,太珍贵了。
后来会发现, “钱”关乎农家子弟家庭的付出和牺牲。他们习惯性地用学习来回报家庭,把学习作为一种道德事务来看待。一位农家子弟在访谈中说他想毕业后去支教,再出国留学,但考虑到父母,就觉得自己必须要找一个很稳定的工作。这样,他把自己的真正心意藏了起来,懂事、克制、也同时压抑着自我。

北师大里的年轻学子,正在庆祝毕业
爱情
农家子弟的爱情是一个敏感问题。这其中关涉一个我不太喜欢的概念——凤凰男(女)。因为这个词常常把农家子弟的成长变得单向度,成了一种贬低、剥夺和限制。而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有值得敬重的地方,也各有其局限。
在南方读博的溪若说,她不配拥有爱情,“谈恋爱要花很多钱的,难道我都要让男孩子来付吗?”
男孩子的自卑心会更明显,很多时候是暗恋。秋敬的父亲在老家务农,母亲做小生意。他在学校和一个城里姑娘交往,每次约会都会很紧张,不知道该如何与她相处。他说“我平时情商蛮高的,但和她在一起,如果说我原本的情商有100,现在就剩下50了。”
在一次读书讨论中,一个城里长大的女孩说这本书让她更理解了自己的伴侣。也有人说,这本书让他们从中理解了自己的父辈。
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遭受歧视的地方,也许是出身、也许是学历、也许是身高、也许是性别。不把人标签化,是一种尊重,也导向自由。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正在看书的少年
故事的另一面
在很多人眼里,这群通过教育阶梯、一步步奋力前行、最终很可能走出农村,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农家子弟颇为励志,但我想说这只是故事的一面。他们自身道德、情感和文化世界面临着一次次的冲击,这其中也隐藏着风险。
羞耻感
夏风是一位重点大学本科生,21岁,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务农。在自传中,她记录了一件最让自己感到羞耻的事。小学时曾经在作文书上抄了一篇《洗抽油烟机》,老师一眼就看出来是抄的,还在作文旁边做了批注,因为按照她家的经济情况不可能有抽油烟机。

还有一个男孩溪泉说,他会刻意不和同学说起自己父亲的职业,只因他是农民。
青阳在北方一所重点大学读博,父亲务农,母亲做着小生意。他说自己成长过程中总能听到有人会用“农民”“农民工”来取笑一个人穿得比较土。虽然没有取笑他,可是每次听到有人这么说,他的心里都会升起异样的情绪。他也被刺痛了,觉得自己好像连带着被取笑了。因为对这些农家子弟而言,农民和农民工就是他们的亲人和家人。

农村出身会刺痛我们,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安慰,甚至感觉到骄傲。
曾经和一位家境比较好的朋友聊天。她在城里长大,家里之前给的支持比较多,一直不怎么缺钱花,工作后开始不好意思拿家里的钱,又要租房子、要交际,一下子觉得自己变穷了。
而对许多农家子弟来说,工作后一般都会比大学时做家教或者勤工俭学等方式挣的钱多,因此会有一种“有钱”的感觉,甚至还会反哺家庭。
不管是大学时做家教还是工作后拿到工资,我会觉得自己挣的钱和父母给的钱是不同的。用自己挣的钱会感觉轻松,因为这些钱不再是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来的了。

在故乡成为异乡人
“爸爸帮不了你了”“父母帮不了你了”,听到这样的描述,是最心痛的。在我采访的对象中,大多数人明确表示自己父母的付出不比中产父母少,他们同样是倾其所有。
一位农家出身的硕士毕业生在毕业论文后记里写道,“我最该感谢的人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没有进过学校校门的农村妇女,却集中了传统中国母亲的几乎所有优点。”没有母亲的苦心经营,他大概初中毕业时就得被迫辍学,进入生产车间劳作或在田间劳动。
但随着这群学子突破人生道路,他们就成了和父辈不同的群体,双方都难以进行实质上的沟通。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使得他们和很多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乡邻之间,在观念上存在一些差异。

云隐是在国外读博的一个男生。室友会和父母聊各种学习上的事情、人际上的事情,甚至谈恋爱的很多细节,每次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而云隐自己和父母的聊天总是5分钟、10分钟就尴尬地进入聊亲戚、天气,说到最后就变成了嘘寒问暖—— “妈,你晚饭吃了啥”。
溪若读博时回乡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班上学历最高的人。聚会时大家都在讲“我公公怎么样,我婆婆怎么样,我家女儿儿子怎么养”。同学对她的高学历并不羡慕,也会跟她说“学得好不如嫁得好”。
故乡的文化样式、曾经关系紧密的人逐渐离自己远去,他们感觉在故乡成为了“异乡人”,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 Simmel)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他说“异乡人是潜在的流浪者”。

2015年,程猛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学
在网络上,许多农家子弟也会倾诉在城市奋斗的苦恼。
他们基本都是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走在了一条家里所有的人都未曾走过的道路。大学选专业首先就是两眼一抹黑,像我的专业“社会工作”是我填的第四个志愿,当时一个朴素的误解是,如果学了这个专业,是不是以后社会上的工作我都能做了?
我和溪若进行了4次访谈,说到最后,她说“自己对爸妈从来都只有小小的怨”、“过去的我都不在意”。

图片来源网络
一个自我重塑的故事
从2011年起,一个网友就发起了关于“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讨论。在李春玲老师的研究里,在80后群体里,城里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四倍。
现在城市里一直有 “学区房”这个概念,你买得起好的房子,你的孩子就能接受好的教育。
在小城市和县城,优质的生源、优质的师资也很容易往更中心的城市流动。比如说在某些省份,不进入省会城市最好的几个高中,就几乎与最好的大学无缘。

外面的世界,通过手机渗透到了农村,摄影师刘飞越作品
也有科技的影响。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以前是游戏厅,现在是抖音就可以滑一天,也很容易沉迷各种网络游戏。曾听闻一位乡镇上的中学校长说,“这些孩子我们坚决不能让他玩手机,不用手机他们大多数人还能考上高中,如果用了手机的话就考不上高中”,他讲得很直接。这需要我们去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引导农家子弟去合理地使用媒介,可以依靠谁去引导学生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成长。

图片来源网络
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肖生克的救赎》。作为农家子弟个体,在泥沟里还是要倔强地仰望星空,至少保有一些这样的念想。甚至门关上了,还要努力去找窗。窗关上了,还要学主人公安迪,去挖个洞。哪怕要走下水道,遭遇各种阻碍和绝望,最终也要奋力在大雨磅礴的夜里重见漫天星空。
在不同场合分享这项研究之后,有读者来信分享了自己作为“读书的料”的相似经历,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一些内心的褶皱被看见和抚平。有读者说自己“难以言说的阴翳被温和地化解了”。也有读者述说了自己的体验和书中描述的有差异,帮助我看见更复杂的成长。
在讲述这些农家子弟的故事时,我会担心自己写得太沉,没有凸显这种生命体验特有的光彩。我也会怕写得太轻,遗忘了苦痛和泪水。最终,我把它当作一种对“过去”的理解,让我们的过去有意义,是我们理解自己、并通往未来的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书里面所讲述的这群80后到95后的农家子弟,事实上每个人生长的地方,自己的家庭,包括所经历的都不一样。在我们那边,像80年代,那时候还没有外出打工的大浪潮,有的也只是少数,孩子一般留在农村。但到了1990年以后,一些留守的儿童会跟打工的父母一起进入城市,在很小的年纪就体验到城乡发展的差距。
城乡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可能未来的农家子弟就不会再有这本书里面所写的体验。对于如今的00后、10后来说,从农村走到城市也越来越不再是一个“向上流动”的故事,乡村的发展潜力在不断重新被看见。

程猛近期拍摄的家乡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这些都很重要,某种意义上也是很伟大的。
随着我们的城乡的差异不断得到弥合,农家子弟的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经验将会变得不一样,在这场漫长的旅程中所受到的冲击也会得到缓释。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光彩,也有局限。希望这些故事,能不扰人清梦,却能够触动你的内心,引发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