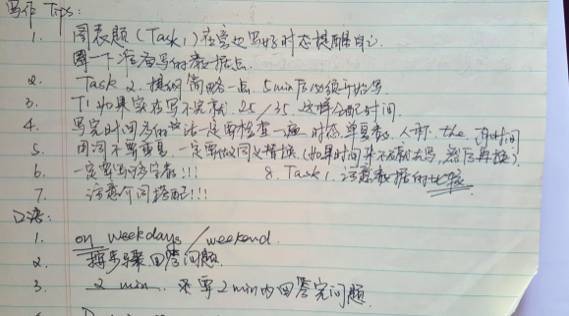■路来森
《书鱼繁昌录》,收录谢其章先生文章29篇;时间跨度,自2001年至2014年,其中多数文章,为近两三年所写。
文章,分为三辑,也只是大略为之。就其涉及话题,实在是极其宽泛,诸如:关于书籍的相关知识:毛边书、线装书,藏书票、藏书印,护封、腰封等;记录个人搜书、淘书的经历;记述书籍的收藏、拍卖情况;民国漫画、私人日记;书评、序跋;以及对特定历史现象和事件的探讨分析等。
如果,勉强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该书忠实记录了谢其章先生近几年的“藏书经验,和阅读心得”。
“经验”,仅供借鉴;“心得”,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能看得出一个人学识修养,更能见得一个人“识见”的高低。
喜欢藏书的人,都有自己的“猎书”经历;人各不同,其经验、感受,自是各有不同。谢其章先生,在文章中写自己的“猎书”感受:“夜里,静坐在孤灯下,一本本地整理白天从旧书摊捡回来的几摞书,擦掉书上的灰尘,补齐封面的缺角,抹平书页的折痕,那情景,与孤儿院院长为捡来的孤儿洗澡、穿衣、理发,庶几近之。”一般人,大多喜欢,津津乐道“猎书”的过程,而谢其章先生,却独写“整理旧书”的那份感受,字里行间,都流淌着一种暖暖的书之爱意。
姜德明先生,三十年如一日坚持写“书话”,曾一度引起争议。有人就此,评价姜德明先生写作“保守”——那言外之意:“书话”谈不上什么大文章。对此,谢其章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书话,是一门特立独行的文章形式,不可能像散文那样人人都能写。书话写作的首要条件是作者必须自存自藏一大堆旧书刊做资料后盾。(不非得是汗牛充栋的藏书家,至少也是藏书爱好者)”不仅充分肯定了“书话”文章的特有价值,而且掷地有声,旗帜鲜明地肯定姜德明先生的写作:“不是保守,是坚守”。
老民国“旧报旧刊”,一向是谢其章写作研究的关注重点,也是他写作研究的基石所在。以此为基础,对一些历史事件、现象的存疑,进行揭秘、解答,就成为谢其章文章,最为可读的一部分。本书中,这样的文章,亦是最大亮点。
1942年,梅兰芳是如何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此一问题,多有争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张爱玲的一段记载。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回忆她从香港回上海,是和梅兰芳同船的:“她立刻想起回上海的时候上船,珍珠港后的日本船,很小,在船栏杆边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一行人,众星捧月般的围着个中年男子迎面走来,这人高个子,白净的脸面,细细的两撇小胡子,西装虽然合身,像借来的,倒像化妆逃命似的,一副避人的神气,仿佛深恐被人占了便宜去,尽管前呼后拥有人护送,内中还有日本官员与船长之类穿制服的。她不由得注意他,后来才听说梅兰芳在船上。”似乎言之凿凿;但谢其章,却充分利用1942年8月8日的第一卷第三十期的《太平洋周刊》的“本报专访”,证明梅兰芳是于1942年7月26日在“大场飞机场”下机的。于是,一切疑问,豁然开朗:“梅兰芳是乘飞机回到上海的,那么张爱玲在船上看到的那个人绝不可能是梅兰芳了。”
“南玲北梅”事件,一度喧嚣。此前,止庵、赫啸野等人,都曾撰文,证明其荒谬性。谢其章在《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一文中,再度充分利用大量详实的资料,并附上“北梅”“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奖”的受奖照片,证明了“北梅”言论的极大荒谬性。他说:“对此,我不得不拿出这张梅娘领奖的照片,真是抱歉的很。在真相面前,谁也没有特权。”就此见得,所谓“北梅”的梅娘,不仅“早节”不保,“晚节”更是荡然无存了。
书中,“心得”尚有多多。比如,谢其章对“书画无偿捐献”的疑义,对收藏界“富则俗”的看法,对电视收藏栏目“人来疯”现象的分析等等,都彰显着作者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分析。
而这些观点,又无不以其丰富的图书收藏和阅读为基础;归其大类,这些文章,到底还是“书话”类文章;所以,也正应了谢其章自己的那句话:“书话写作的首要条件,是作者必须自存自藏一大堆旧书刊做资料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