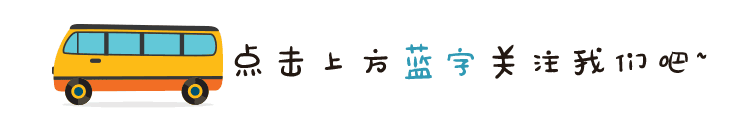沈晴

今年,湖州小梅村最后100户渔民,将完成安置房分配,告别祖祖辈辈风雨漂泊的日子。
蜿蜒的南太湖岸线上,地标建筑月亮酒店一带,就是渔户当年停船的地方。1960年寒风乍起的那个秋天,36户祖籍苏州的渔民在湖州渔业联社的动员下,携家带口迁往一水之隔的浙江。他们多驾着三根桅杆的拖网船,操帆娴熟,打渔高效。
慢慢的,南太湖的三个水产村,作业方法互相渗透,捕捞工具与时俱进,渔民收网时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鱼一年比一年少了。
2000年前后,整个环太湖城市群开始坐上高速列车,苏锡常高楼拔起,沿湖的工厂直排废水,让平均水位三米的太湖泛起了浑浊的浪花。直到2007年蓝藻大爆发,从受灾最重的无锡,蔓延至其他城市,积重难返的治水困境,成了整个太湖的紧箍咒。
这一年,湖州启动太湖岸线综合治理工程。南太湖边25个自然村1600余户人家全部搬迁,包括整体上岸安居的小梅村。
53岁的沈伯冬当了20年小梅村支书,眼见着渔民两手空空上岸,如今住上了楼房,再也不用担心“三面朝水”,连睡都睡不安稳。
而经过十年治理,他童年印象里可以畅快游泳的太湖又回来了。“风平浪静的时候,它就是碧绿碧绿的,浅的地方能看到水草,有小鱼游来游去。”沈伯冬说,过了清明,看涨水,就能知道今年的渔获如何,“涨水鲚鱼缩水虾”,这是渔民一年中的头等大事。
从苏州来的“大历帮”
南太湖东、西苕溪的出口处,梅子漾、小梅口、丘城山三个自然村组成了最初的小梅村。村民多是50年前南下的一批苏州籍渔民,以沈、黄、姚为三大姓。
“解放前,太湖一带不讲什么村,都讲什么帮,在一起捕鱼的就是一个帮。”沈伯冬是家里唯一出生在湖州的孩子,从小父母就告诉他,沈家的根在苏州大历山,所以小梅村的渔民都自称“大历帮”。

“靠天吃饭,靠风发财”,是这个帮派的生存口号。人力操帆的年代,每一时刻的风力、风向都牵动着渔民神经。为了获得更好的收成,越是有风、有雨,越是天冷,他们越要出去捕鱼,因为刮风下雨船速快,而冬天鱼群减少活动,容易一网打尽。沈伯冬记得,那时他跟着父亲去湖心,一个浪打到船上,就是一条冰棱。
渔民都觉得,在太湖讨口饭吃,比在岸上种几亩地,苦多了。
但他们从不向太湖过分索取,起风了,他们迎风撒网,风停了,他们也歇下了,日子过得简单而知足。2011年落成的渔民新村文化礼堂内,陈列着各种渔用工具,有一张网就是沈伯冬的父亲用过的,网洞密而大。“冬天湖里有冰水,这个网下去,不管鲫鱼、草鱼,还是百来斤的大鱼,都能捕上来。”他得意地向人介绍,如今会织这种网的人少了,秘诀是要让小鱼漏下去。“没有小鱼小虾,哪来大鱼大虾?”
那段时期,渔民捕捞强度不大,只靠风力没有机械化,加上太湖水质良好,渔业资源丰富,小梅村渔户总体收入都不错。比起岸上油水不足的农民,沈伯冬天天都能吃上肥美的湖鲜。
时间一长,渔民还摸索出了独到的捕鱼之技。当地人称一种海鸥为”呆鹅”,这种候鸟喜欢跟着船飞,守在起网瞬间迅速叼走大鱼。“高踏网还没有起网的时候,如果鸟很多,我这一网下去就是丰收,如果边上没鸟,肯定产量不高。”这方面,沈伯冬打心里佩服,“动物很有灵性的,有鱼的地方它很敏感。船老大是凭经验,看风看水流,预测鱼群去哪儿,在哪个地方下网。那些鸟也是凭经验。”
但很快,田园式的渔猎记忆停留在沈伯冬13岁那年,改革开放的前夜,村里开始制造水泥结构的渔船,并使用挂桨机械作用。马达声日夜作响,飞鸟走了,鱼一船一船被拖上岸。

太湖病了
小梅村渔民的一天,大多是从早上给渔船“洗脸”开始的:拿拖把擦一遍船,以免大量露水残留。只是不断爆发的蓝藻以及泛黄的的湖水,让世代喝着太湖水的渔民,遇上了无水可喝的窘境,糟糕的水质连洗衣服、洗菜都嫌脏。他们都知道,太湖得病了。
早年湖州粗放的开发模式,使得太湖接纳着来自东、西苕溪的采矿、工业、农业以及生活污水。湖州市环保局曾测算,石矿企业清洗石料导致太湖淤泥沉积,河床在35年内抬高了两米。
渔业资源的萎缩和水体生态的退化是同步的。在沈伯冬印象中,1985年左右,小梅村光景最好,渔业丰产,银鱼收购价四五十元一斤,全部出口日本。等到他1997年出任村支书,太湖已经暮气沉沉——浅滩边的水草被闷死,“太湖三宝”断崖式减产,价格再也没升回去。“水质不好的话,珍贵的鱼就少,太湖里的鱼我觉得桥头鱼最好吃,可惜很多年都没见过了。”沈伯冬叹气。
“表面在水上,根子在岸上。”太湖旅游度假区(下称“度假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葛伟多次对媒体表示,“过去,我们廉价出卖了祖宗留下的青山绿水,养了一大批‘愚公’。”

如果没有2007年那场轰动全国的蓝藻危机,整个太湖流域还处于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怪圈。那年5月,太湖爆发严重的蓝藻污染,无锡受灾最重,部分水域像绿色油漆般浓稠,造成全城自来水污染长达一周。
从太湖治水的十年经验看,外来污染源得不到削减,湖内做再多的防控都是末端治理。
2007年10月初的16号台风“罗莎”,成为湖州大力推动南太湖综合生态治理的转折点。往年一到台风季,渔民都提心吊胆,休渔进港不说,身家财产也受到威胁。那场强台风掀翻了小梅村五条渔船,1954年出生的姚国庆半生漂在太湖,从没见过这样狼狈的场景。
“浪头很大,3米多高,缆绳全部断了,百吨重的水泥船都翻身,倒下去了。有人打电话叫我帮忙,我骑了个自行车过去,哪里骑得动,把自行车扔在边上,像解放军一样走!”他说,靠太湖吃饭的人,从不敢小觑大自然的力量。

为加快太湖的自我修复净化,多年来,太湖旅游度假区累计投入20亿元,全面清理环境污染源头:搬迁关闭12家中型以上规模工业企业;拆除低小散家庭工厂作坊300多家;清除太湖水面和周边水域养殖围网1000多亩;整体改造湖鲜一条街25条水上餐饮船。
湖鲜一条街曾是小梅村的核心集体资产,1997年村里负债累累,账面上只有13.5块,沈伯冬顶着压力抵押了自己的一套房,筹资十万元开建。十年后为了动员拆除,他又率先关闭了和哥哥合营的餐饮船。谈到小梅村的十年得失,村民的心情都是复杂的——既失落于传统生活的遗失,又憧憬岸上的安稳生活。
“渔民住在船上,陆上一寸土地都没有,为了支持太湖治水,放弃了很多。”沈伯冬感慨。
渔民上岸
小梅村的渔户都有两条船,一条捕鱼,一条住家,就是在船上盖间低矮的屋子,只够猫着腰进出,摇摇晃晃从来没有一刻平静。船上的孩子没什么娱乐,夏天跳水里可以玩一天,爬桅杆是少有的游戏。只要船一靠岸,他们就像出笼的小鸟,凑在一起打弹珠、滚地龙、抽陀螺——宽敞、平静的陆地,是逼仄、晃荡的船上空间的反面。
到了上学年纪,没有房的渔户只能把孩子送到丘城山上用渔改房建的小学。沈伯冬小时候就寄宿在农村亲戚家,每天守在太湖边,看自家的船来了没有。“感觉跟同学不一样,寄人篱下,和父母相处时间也少。”跟他同辈的人几乎都有一种想法——好好学习,赶快离开船上。
因为没有房产,渔民的儿子往往娶不上媳妇,女儿出去了就不回来。姚国庆说,因为圈子小,“岸上的好人家也不愿意女儿嫁到船上来”,过去渔民近亲结婚多。年轻人但凡能读书出去的,一般不再回来。


上岸,是渔民多年的呼吁,这个愿望在2007年因蓝藻危机终于迎向了曙光。按照规划,度假区将投资近3亿元实施渔民居住上岸工程。四年后,第一批渔民新村拿到了新居的钥匙,以每人25平米的标准安置,独生子女算两个人头。“加上补贴,平均870元每平米,100个面积只要八万七,现在我们周边房价都1万多了。”说起房价,村民都显得很兴奋。
第一次在独立的厨房烧饭、第一次在客厅看电视、第一次在楼房过夜……哪怕50平米的一居室,也是足以顶天立地的家。
但随之而来的,是甜蜜的烦恼。当生活从平面的太湖,来到立体的高楼,日常习惯的改变对身心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渔民临水而居,又自小盘坐,多有关节炎症,跟村委会频频倒苦水,“爬楼梯不方便”。自来水要收费,节俭的渔民就拿着拖把、衣服去临近的河边洗。村干部苦口婆心地劝,年纪大的渔民一赌气,吵着要回船上去。
沈伯冬的母亲刚搬进50平米的楼房时,也跟他抱怨,还是习惯船上的日子,假如政府允许买船,她还是要回去的。但这几年他又问起母亲,她已经宽心许多。“不回去了,这里刮风下雨吹不到,也不用半夜起来加固船舱,现在都不用考虑了。”
重回南太湖
小梅村258户1067人全部上岸后,从事传统捕鱼的仅剩30多户。有人改行去了东太湖养蟹,有人被度假区雇佣,在景区开快艇、帆船或者打捞蓝藻。村口一块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石头,见证了绿色湖州的十年变迁。
33岁的施冬牛在服装生意亏本后,又回到了太湖谋生。“这边稳定的话,开快艇一年能有七万,就是夏天晒得比较黑,反正我结婚了也无所谓。”他推了推鼻子上的墨镜,笑着说。“落叶归根,还是离不开这边,到别的地方去也吃不开。”
每年5月1日,哪怕是在外打拼的小梅村人,都会看两眼天气预报,关心下太湖的涨水,就像他们的祖辈那样,按时回归渔民的身份。这天春季捕捞启动,拖着长尾巴的“地笼王”、小钓船、钓钩船一一上阵,在休渔期间捕捞小型鱼虾。
真正的高潮在9月6日,大型渔具高踏网登场,开始为期25天的捕捞。它长约1500米,宽约2米,网目约0.5厘米,待湖中设置起鱼用的鱼箱网,两艘渔船牵引大网的两头收拢,并将网中渔获全部赶入箱网内,起网收鱼,一网产量最高可达5万斤,一般一艘渔船一天能捞上20吨湖鲜。
“‘飞机网’、拖网,从9月捕到11月底;如果有‘鱼蛋’(迷魂阵)的话,可以捕到12月底。”沈伯冬介绍。
气候逐渐转冷,休渔期漫漫,渔船都回港了,只有12艘仿古帆船在湖心巍然不动,仿佛即将启程的船队。

姚国庆是其中一艘船的管理员,度假区以每月约3000元,聘请他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他清楚地记得,他的船是2011年4月23日从江苏买来的。
“管理这个船很不费力的,都是我小时候就懂的。不像我儿子,小船的缆绳打个结都打不好。”他露出懊恼的表情。去年,他儿子没打好结,浪打来让小船漂走了。“这个结有讲究,要系得不散,但又很容易抽掉,这样我们晚上摸黑也能解开,否则晚上你要拿剪刀剪、拿刀砍,很麻烦的。”姚国庆说,这个系结方法对渔民来说并不难,但儿子就是怎么也做不好。
沈伯冬知道,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角力中,属于渔民的日常终将退守至记忆的边缘。方言是这群渔民三代,与太湖仅剩的薄弱联结之一。“太湖里的渔民有自己的方言,和苏州话相似七八分,和湖州话相似二三分。”他有时觉得,只要孩子还会讲家乡话,那他们这一代就不会忘了自己的根。
“我们都喜欢吃鱼,每天都要吃,吃不到难受。”这让沈伯冬稍感欣慰。去年,有渔民幸运地捕到了太湖里绝迹多年的桥丁鱼,他央求人家把30斤全卖给他。“就是比笔粗一点,只有一根骨头,其他都是肉,入口最嫩。”他给发小每人送一点过去,他们都说,跟小时候的味道一样。
上岸十年后,他最爱的桥丁鱼又回来了。
(图片如无说明,均为本报摄影记者任玉明、吴军、胡军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