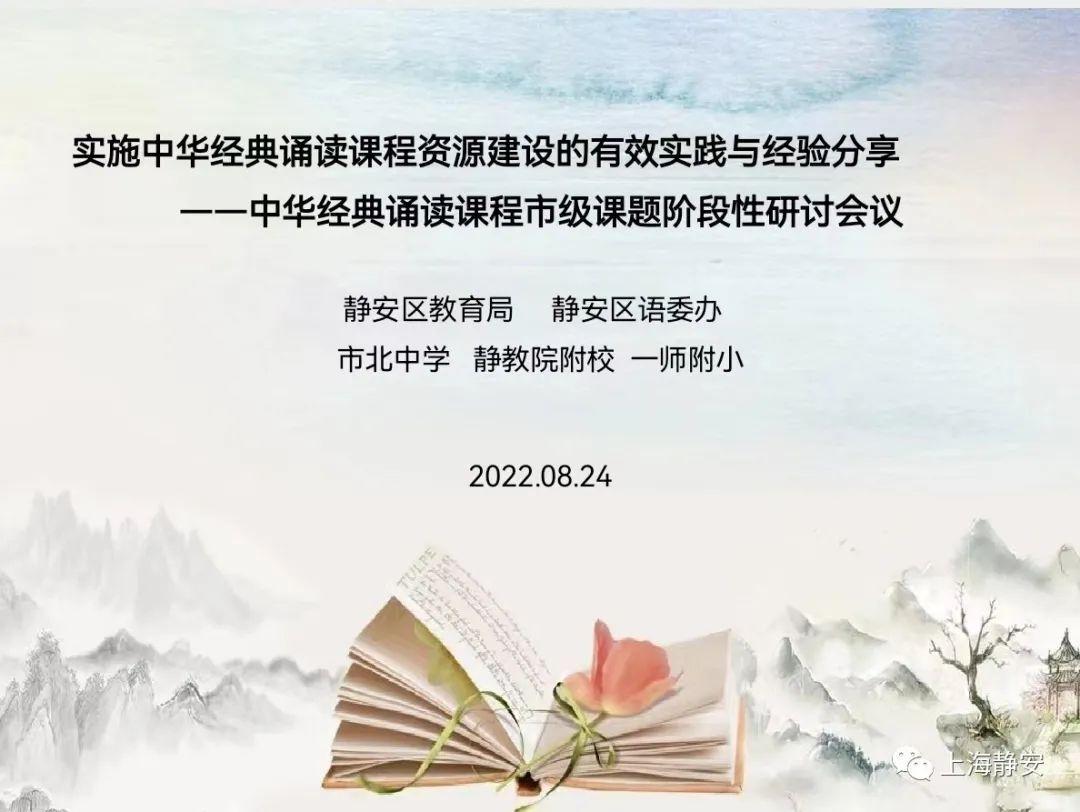法籍华裔画家赵无极(1920-2013)的特展“大道无极——赵无极百年回顾特展”这些天正在西湖之畔的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对外展出。在作者看来,不能简单地用“抽象”两个字来涵盖赵无极的艺术世界,但同时,我们不能免俗,还是不知不觉地会把赵无极称之为“抽象艺术家”。
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位完全融入西方现代主义的抽象画家。无论是赞赏者,还是诋毁者,都倾向于将他与中国传统割裂开来看。然而赵无极曾这样说:“谁能了解,我花了多少时间来领悟塞尚和马蒂斯,然后再回到我们传统中我认为最美的唐宋绘画?”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抽象”两个字来涵盖赵无极的艺术世界,但同时,我们不能免俗,还是不知不觉地会把赵无极称之为“抽象艺术家”。前一段时间,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假装看懂赵无极”。一旦涉及到抽象,我们就会遇到很多问题。
(一)
面对一幅抽象画,我们能进入的“路径”很少,以至于很难对抽象画家进行视觉欣赏之外的评述。尤其对于像赵无极这样一位坚信自己在绘画中已经完全表达清楚、无需语言讲述的画家。同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注意到,赵无极无时无刻不在寻求语言的陪伴。他与法国诗人、评论家们如影随身的同行,与他们之间(亨利·米修、勒内·夏尔、克洛德.鲁瓦等)几乎规律性的“对话”,让人看到,语言——至少是诗性的语言——是他绘画作品的“另一半”,是作为绘画“不言之意”的回声。诗与画“同框”,乃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大的特点。赵无极的绘画,不与诗“同框”,却与诗“同在”。同处一种场域之中,或者指向同一种方向。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诗与画的“对话”或潜在对话,让我们看到进入赵无极抽象世界的某种“路径”:假如诗是他绘画的镜子,那么,他的绘画,也是某种诗的镜子,隐隐约约地和诗形成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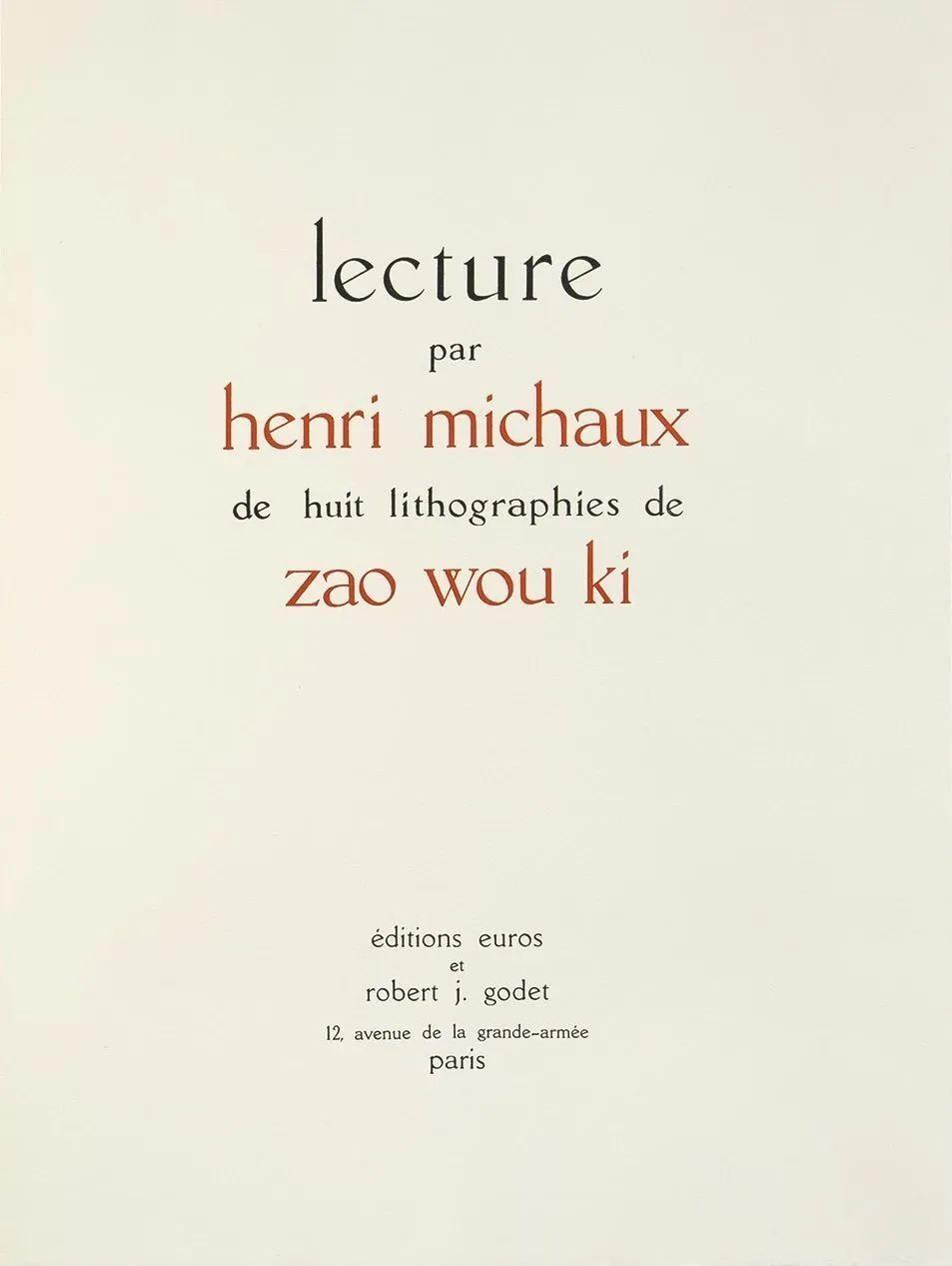
赵无极,《亨利·米修解读赵无极的八幅石版画》(Lecture par Henri Michaux de huit lithographies de Zao Wou-Ki)1950年,45×65 cm 摄影:Antoine Mercier

“大道无极——赵无极的艺术世界论坛”现场
赵无极的绘画作品,即便是看似随意涂抹,也有着一种难能的清澈;赵无极的文字讲述,即便是时常陷入沉默,也有着一种罕见的明晰。因此,他与夫人弗朗索瓦兹.马尔凯合著的《赵无极自传》,成为进入、甚至穿越赵无极艺术世界的极佳路径。赵无极从来没有给自己画自画像,选择了用文字给自己作自画像。书里有一句话,“我渐渐明白,我的画反映着我的经历”。从《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赵无极对自己的艺术生涯的分段,更多建立在自己生命中的重要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灵震动之上。这一做法,其实与他一生的好友亨利·米修暗合。亨利·米修生前出版过著名的《五十九岁简历》,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历程融合到了一起,赵无极的《自传》也是向亨利·米修的致敬。

赵无极,《向我的朋友亨利·米修致敬,1999年4月-2000年8月——三联画》(Hommage à mon ami Henri Michaux, avril 1999-août 2000-Triptyque)1999-2000年,布面油画,200×750 cm
(二)
赵无极到了巴黎之后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不想搞中国玩意儿(chinoiserie)”。这样一种宣言,值得我们细细体味。事实上,它并非意味着与中国的决裂,而更多是与所谓的“法国传统绘画”拉开距离,因为“中国玩意儿”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传统美学立场的概念。正是法国画家们,让“中国玩意儿”得以凸显,风行一时,并成为某种装饰风格的代表。而这种装饰性,是赵无极一生的艺术追求所摈弃的。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摈弃“中国玩意儿” ,一方面又要让人们想起博大的中国。青铜器、甲骨文、唐宋气象,这些都是赵无极心中的中国,是他想找回的中国。
赵无极特别强调,他是诸多同学中,唯一去法国的。他用心良苦地传授:“谁能了解,我花了多少时间来领悟塞尚和马蒂斯,然后再回到我们传统中我认为最美的唐宋绘画?”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当时在许多人眼中,他是一位完全融入西方现代主义的抽象画家。无论是赞赏者,还是诋毁者,都倾向于将他与中国传统割裂开来看。赞赏者欣赏他融入世界,开现代之先风,诋毁者批评他脱离传统,成为无根之萍。《自传》恰恰是面对这两种态度最好的回应。

赵无极,《向塞尚致敬》(Hommage à Cézanne)2005年,布面油画,162×260 cm 摄影:Dennis Bouchard
确实,很少有中国艺术家像赵无极那样,从一开始就如此决绝地、自发地远离中国绘画教育环境,如此全面地拥抱方兴未艾的西方现代主义潮流。“为什么你一到巴黎就结交了那些现在博物馆竞相展览、出版社竞相为之出书的艺术家,还有那些现在都成了大作家和名医的朋友呢?巴黎很大,他们可并不是集中在一个房间里的……”这是他妻子马尔凯经常问他的问题。赵无极对此的反应是:他本人也不知如何回答。现代法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十字路口,一个熔炉。它是法国,又不仅仅是法国。有狭义的法国,更有广义的法国,而广义的法国,是现代、开放的代名词。法国——赵无极所处的法国——从未要求人们爱上狭义的法国,而是以广义的它,容纳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这是现代艺术的幸运,也是赵无极的幸运。
《自传》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远非艺术家对自己实际生命历程的罗列,而是自己心路历程的展示。在这一心路历程中,除了与自己的家庭密切相关、深度触动他内心从而导致艺术表达的转变的几件大事,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艺术家的相遇与共处,成为伴随他一生的重要事实。这些事实,上升不到“事件”的高度,却时时树立起多元的标杆,让他屡屡实践“以人为镜”这一中国传统的为人之道,在世界的多元之声中,更为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独特。
(三)
年轻的赵无极到了巴黎,短时间内认识了后来名满天下的艺术家和诗人群体。
当我们俯身细看赵无极在巴黎的“朋友圈”,看他所处的“巴黎画派”,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画家们后来的成功,已经几成定局。他们所带来的,以及他们所探索的,正是战后巴黎所需要的,也是战后西方所需要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就在艺术史专家们齐声强调现代艺术的中心已从巴黎移到纽约的同时,赵无极与他身边的“巴黎画派”,执拗地、顽强地、几乎无声地告诉人们:巴黎依然是中心,或者至少是两个中心中的一个。但凡曾在MOMA博物馆里徜徉、在它丰富浩瀚的抽象收藏前赞叹不已的人们,都会产生一丝可惜:这收藏是那么的震撼人心,却也是那么的美国,那么的纽约,像赵无极那样的作品在其中的缺失,留下的是一个过于显著的缺憾。也正是在这种缺憾感中,赵无极独一无二的价值,脱颖而出,“巴黎画派”的价值,也同时凸显。

赵无极, 《无题(有苹果的静物)》(Sans titre [Nature morte aux pommes])1935-1936年,布面油画,46×61 cm 摄影:Antoine Mercier
事实上,如果我们认同“巴黎画派”这个过于宽泛的说法,那么,赵无极所属的,已经是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巴黎画派”。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新巴黎画派”。老的巴黎画派中,涌现了一大批大艺术家,他们自1900年左右起,就开始在巴黎扎根,让巴黎成为真正的艺术中心,其中许多成员来自中欧、俄罗斯,尤其是有大量的犹太人。新巴黎画派成员的来源,远远超出了欧洲范围,具有真正的世界涵义,而在老巴黎画派中,即便有藤田嗣治这样来自远东的艺术家,也几乎是孤例。如果说,老“巴黎画派”的艺术追求,还比较受到巴黎当时的艺术氛围的影响,那么,新“巴黎画派”的成员,已经开始对由马蒂斯、塞尚、毕加索等人开拓的现代艺术进行某种反思,而其赖以反思的资本,往往是每个人从自己所处文化带来的相异性。仅举一例,就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2003年,赵无极的好友、加拿大画家里奥佩尔(Riopelle)去世。2008年,赵无极的巨幅作品《致敬我的朋友里奥佩尔》(2003)在加拿大展出。策展人在序言中,特意提请观众关注赵氏抽象与里奥佩尔抽象的明显差别:一种是来自东方的、深邃的沉思型抽象,一种则是密集的、令人感受到加拿大暴风的力量型抽象。

赵无极,《15.01.82 - 三联画》(15.01.82-Triptyque)1982年,布面油画,195×390 cm
新“巴黎画派”的这种世界性,需要一种新诗学的支撑。对应于马蒂斯、毕加索,诗人的代表无疑是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桑德拉尔斯(Blaise Cendrars),以及超现实主义者们;对应于新的“巴黎画派”,我们有克洛岱尔(Paul Claudel)、米修(Henri Michaux)、夏尔(René Char)等。前两人的诗性是横向的,是对水平线的拓宽,后者的诗性是垂直的,是对古希腊、罗马的再考。但两者具有相通点,就是对自然元素、对空间(内、外,无限)的强调。元素性、内在性、宇宙性、精神性,成为新趋向。亨利·米修打开的“内在空间”,保罗·克利开拓的符号世界,为经历个人痛苦的赵无极,带来全新的可能性,即便对克利的追随,让赵无极几乎一度迷失。
巴黎作为熔炉的意义在于,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感受到了全新的艺术追求的需要。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在刺激、在召唤着艺术家。马蒂斯、塞尚、毕加索等人达到的成就与世人的承认,将艺术家放置到了可以说史无前例——如果我们看今日之艺术,也可以说是后无来者——的地位。不再是“自由引导人民”,艺术家已俨然接过了自由的旗帜,成为开拓者、引领者。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赵无极的中国背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
(四)
对克利的喜爱,对于赵无极来说,带有对中国的回望。在他看来,克利一定对中国绘画十分了解,才会创作出这样的作品:“他(克利)对中国绘画的了解和喜爱是显然的。从这些描绘在多重空间里的小小符号中,浮现出一个令我叹为观止的世界。”这也许是第一次,西方绘画向赵无极暗示,在他自己的文明中,有一种鲜活、生动、现代的东西,在等待人们去挖掘。“西方绘画——眼前(克利的)这幅画是最纯粹的例子——就是这样借鉴了一种我所熟悉的观察方式,而这种方式曾使我疑惑。”他曾经不愿意接受、希望与之保持距离的过于熟悉的观察方式,原来是可以被西方绘画所借鉴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新的世界。

赵无极,《锡耶纳广场》(Piazza Siena)1951年,布面油画,50×45.5 cm M+博物馆藏,中国香港,2020年赵善美女士捐赠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探索对于赵无极的触动和推进作用是决定性的。向几位精心挑选的法国现代大师的每一次致敬,对于在绘画的命名上至为严谨的赵无极来说,都是一种新的飞跃。无论是向莫奈致敬,还是向马蒂斯致敬,都是赵无极艺术历程的某种里程碑。反观中国一边,赵无极致敬的,是屈原,是杜甫,即那些在他眼里代表着真正的中国精神的文人。身处法国的现代熔炉之中,赵无极不断地回望(中国),不断地远望(世界),寻找自己真正的“同道”。他开始明白,自己以前对传统的否定,只是一种新的起点,而非决绝的终点。
米修成为他在全新的未知状态中前行的“航标”。正是米修,敏锐地看到了赵无极在意大利之行之后出现的新气象:“忽然间,画面带着中国城镇乡村的节日气氛,在一片符号中,快乐而滑稽地颤动”。赵无极惊喜地回忆道:“符号,正是在这里,这个词第一次出现。”而且,“渐渐地,符号变成了形体,背景变成了空间”。

赵无极,《节日的村庄》(Village en fête)1954年,布面油画,96.5×130.5 cm 摄影:中国美术学院
背景成为空间,这一步的重大意义。最重要的是,这一符号变成形体、背景成为空间的过程,恰恰伴随着文字让位于自然元素的过程。大自然,开始重新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入绘画。皮埃尔·卡巴纳(Pierre Cabanne)在解释“抒情抽象”产生的前提时,敏锐地指出,无论是马蒂斯还是毕加索,尤其是立体派,他们的创新行为都建立在都市经验之上。即便是塞尚、梵高,他们笔下的自然也是欧洲大陆的自然,绘画中始终缺乏一种真正的、堪称大自然的辽远、宏伟景象。抒情抽象正是对这样一种虽然打破了传统的透视法、却依然有所限定的空间的突破。现代绘画在呼唤它的“新大陆”。赵无极带来的中国空间,为打破这种现代都市空间以及建立在这种经验之上的现代绘画空间,带来了无穷的可能性。
巴黎的现代熔炉,还为赵无极带来了另一种强烈体验,那就是色彩。相对于宏大的中国传统,赵无极的最大贡献也许就在于将现代绘画中色彩的力量,灌注到了中国传统画的漠漠洪荒之中,从而让虚空拥有了一种“存在性”。至少是现代视觉可以感知的存在性,从而让虚空成为可以栖居的诗性空间。在西方持久的“线条/色彩”之争中,赵无极有意无意地转向色彩,这是他走出克利阴影的最有效方式。线条经历了从以横竖为主的纤细黑线,到类似甲骨文、青铜文字的痕迹,再到重回大自然中的基本元素的过程,几乎是一种线条自我隐去的过程。线条让位于手势,而手势意味着节律与运动,意味着宇宙的苍茫力量。直至画面上出现越来越大的“空”,而这“空”——除了在以水墨为材料的作品中以白色出现——往往是一种极具感性的色彩。这也是他向马蒂斯致敬的真正原因:“他(马蒂斯)画中提示的那个开口启发了我,真让我有想要进去的感觉。这是单纯凭借色彩走向无限的途径。”
正如诗人博纳富瓦所指出的,这种色彩并非纯色。这使得赵无极没有走向以形式为主的抽象,没有成为蒙德里安,甚至没有成为德·斯塔尔(De Staël)或波利亚科夫(Poliakov)。这种非纯色的探索,为抽象空间带来了打破透视之后的深度:“符号与颜色之间不再有界限,我还从不同色调的结合中,意识到空间深度的问题。”抵达了这一前所未有的空间的赵无极,开始进入人们梦寐以求的“自由王国”,一切都成为涌动,或者涌现。批评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第一个指出了这种涌动:“是颤动中的完满感。是涌现。”与赵无极远没有像米肖那么熟识的大诗人勒内·夏尔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用他带有古希腊回声的诗句,描写这种持久涌动的壮观:“在那里,透着云游者俄耳甫斯琴声的魔力,空灵而有磁性,画面的各个构成因素相互联结,不断蕴生新意,好像夕阳将逝时变幻于天际的缤纷色彩”。赵无极本人对这个说法也深感满意,尤其是这个说法,让他与现代西方人追求的往往以大海为比喻的“无限”实现了和解:“我从未对大海产生过很大的兴趣。……我对西方诗人经常提到的‘无限’的概念也并不敏感。我更喜欢宁静的湖面,隐含着神秘,制造出无尽的色彩变幻”。可以说,在这种时时为新的涌动中,他抵达了某种兰波(Rimbaud)式的永恒。

《07.04.80》1980年,布面油画,152×130.5 cm 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藏,存放地:法国驻华大使馆,中国北京,FNAC 33427
赵无极的艺术历程,按照现代作家们喜欢用的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冒险”。一种生命与精神相结合的冒险。在这一冒险过程中,如何与中国文化中最为精髓、最为博大的精神气息相结合,如何超越时代的局限、时髦的喜好,与中国文化中最具创造性、最具智慧的时代与元素再度连接,在现代的熔炉中展现自由创作的最大可能性,是赵无极的核心的关注点,也最终让他在他所处的世界中独领风骚,成为一个全球现代艺术史中绕不过去的标志性人物。
在《自传》撰写之时,深知离不开世界的赵无极已经可以肯定地对自己说:中国是回得去的。
赵无极的真正回归——他本人未能看到——是进入21世纪后的近二十年。他以他的回望与远望,不仅成为当今中国艺术界的伴随者、引领者,更将以他的作品,成为中国未来走向的航标灯。相信中国美术馆这次规模空前的展览,将是赵无极先生的真正回归,也是弥补赵无极先生1985年“失望”之旅的最佳方式。回望赵无极,远望艺术的发展方向,这是何等令人振奋的事!一个回得去的中国,将是中国与世界艺术家可以共同参照的艺术疆域。
【本文为2023年9月20日,董强在“大道无极——赵无极的艺术世界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原题为《远行与回望——跟随赵无极走进他的抽象世界》,由于作品图版权限制,文中部分配图与讲稿提到的相应作品图略有出入。(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审定,章节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