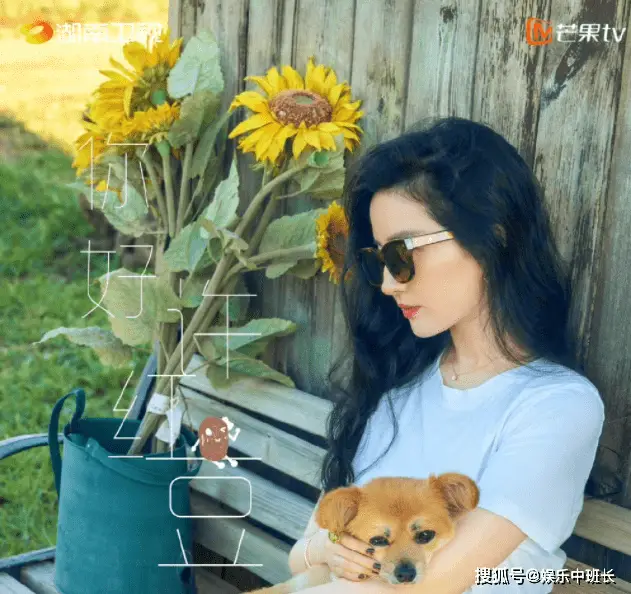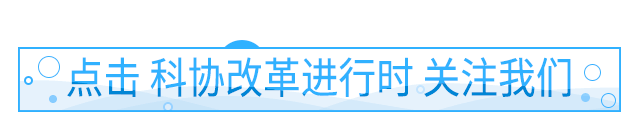在云南古代历史上,大理国和南诏国可能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但另一个神秘的、短暂的、堪与南昭、大理国并列媲美的“自杞国”,却鲜为人知。
自杞国是南宋时期滇东、黔西南地区的一个以“东爨乌蛮”为主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少数民族氏族政权。它既不属于南宋,也不归附大理国,自称为“自杞国”。 据学者考证,自杞国建立于1100年前后,至元初灭亡,前后历时160余年。其疆域大致北至曲靖,南达红河,西抵昆明,东到广西红水河。都城在今天的泸西县境内。

自杞国的创立有着特殊的历史前提。唐天宝七年,南诏灭爨,强大的爨氏帝国瞬间轰然倒塌,并被强行分崩离析。其二十万户(实际数目应该没有这么多)被迫迁徙到滇西永昌(今保山一带)。南诏国灭亡后,云南先后经历了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和大义宁国三个政权的更迭。公元936年,与东爨乌蛮有着血缘关系的段思平借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之兵灭了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东爨各部落分别散居林谷,内部长期保持着自己的氏族组织,部落与部落之间并不互相并吞,往往是部落发展壮大后,分裂出另一部落,散居到邻近的地方去。”也就是说,自宋太祖挥动手中小小的玉斧,将西南诸地划为“化外之邦”后,中原王朝和云南已不再有君臣关系或隶属关系。新兴的大长河、大天兴、大义宁国这些小国,对东爨乌蛮诸部则是力不从心,难于实施管辖权。在长达几百年的时期里,东爨乌蛮地区处于“三不管”状态,几乎都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壮大。大理国建国后,也曾多次对东爨乌蛮进行征伐,但一是遭遇乌蛮各部落顽强抵抗,二是大理国内部大小领主争权夺利,政局和社会动荡不安。就在大理国自顾不暇之际,乌蛮三十七部相继割据称雄。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称“罗殿国”。“些摩徒”各部势力迅速融合,发展壮大,建立了“自杞国”。很快,自杞国东进西突,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独立横亘于南宋、大理之间,俨然一泱泱大国。
在叙述自杞国之前,说一说陆良地区与自杞国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没有直接的史籍证据,我们只能从种种迹象来推测南宋时期的陆良地区,应该属于自杞国的统辖范围,并且是自杞国的重要区域。
一、从地方名称上来看,自唐至元的500余年间,陆良地区先后被称为“夔鹿弄川”、“吾彦甸”、“落温部”,并建有州城“奇思笼城”。而此一时期,泸西作为自杞国的首都地区,称为“弥鹿川”,都城称为“必罗笼城”,师宗则称为“居匿弄甸”,与陆良当时的名称叫法是一致的。(“必罗笼”即弥鹿城,位于今泸西县旧城镇南300米处,群山环抱,易守难攻。现今尚存有古屋、石礅、砖瓦和大鬼主祭祀鬼神供奉祖宗的庙堂宗祠。)
二、连通大理—昆明—广西南宁以贩马和贸易运输为主的邕州(南宁)古道。一条是南线,自大理—昆明—开远—文山—广南—邕州横山寨,其中自开远至广南的路段被称为“特磨道”;另一条是东线,自大理—昆明—曲靖(石城)—自杞国(陆良、师宗、罗雄)—邕州横山寨。东线的邕州古道在陆良境内的路段共有三段,现在依然还存在着:一条位于板桥镇白塔办事处烽火村以东,长约2公里;一条位于三岔河镇龙凤寺北面以东,长约3公里;一条位于马街镇泉丰村以东,长约2.5公里。这些古道均修筑于两山之间的低凹处,宽一般都在1.8米至2.5米间,皆用大小不一不规则的青石块铺垫而成,石块表面非常光滑,并有深浅不等的马蹄印。走向一致朝向东南面的师宗、罗平一带。

三、滇东古长城。滇东古长城是指起自马龙县格里达古城,经陆良、宜良、石林至弥勒县金子洞坡直线距离超160公里、全长300余公里的古长城。滇东古长城是最近十几年才有的称谓,过去涉及这些古城址、古城埂的叫法是“鞑子城”。1999年,云南省与北京大学合作进行《昆明旅游圈规划优化研究》课题调研,北京大学余希贤、云南大学林超民等教授受邀带领一群史学人员,自石林开始,沿着马龙、陆良、宜良、路南(石林)、弥勒一线的崇山峻岭考察后,发现了用粗加工的石料堆筑而成的古长城、古城堡、古石路、石堆、战时祭祀遗址、瞭望石哨所、烽火台、营盘、与古城堡相连的引水工程、成鱼鳞状分布的战墙掩体等遗址。随后界定为“南方古长城”。当时我在广播电视部门工作,我所在的新闻部专门派出记者全程参与了在陆良境内的考察、踏勘,并在陆良的杨梅山、老尖山、牛头山、雨补等地进行了采访、拍摄、报道。随后,新华社、央视、云南电视台、云南日报等媒体都做了报道。但此后,关于“南方古长城”的说法引起了极大争论。云南考古学界甚至重新组织了一批历史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再一次的考察,并形成了与余希贤等人完全针锋相对的结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修筑的?二是修筑的功能是什么?究竟是作为防御的工事?还是划分地界的界石?抑或是村民种田所垒起来的石埂?三是史书记载在哪里?实物证据在哪里?——但这些都貌似长城的石埂,出现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之中,绝非偶然。陆良大莫古、小百户、芳华一带,过去是重要的防御地区,设有多个军事关口,如天生关、石嘴关、木容关。元代还专门在芳华设立芳华县,大莫古设立河纳县。可见其地理位置战略意义十分重要,修筑这样的军事防御设施,可以说是很正常的。
四、现在在龙海山邕州古道沿途,仍然可以见到一些烽火台、古城堡、瞭望台的遗址,传说是为保护商旅马帮修筑的军事据点,推测也与自杞国有关。
综上所述,确定陆良地区曾经属于自杞国的范围,应当是成立的。
现在,我们来说说自杞国的事。它的许多记载同样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杞国人是东爨乌蛮的一部分。关于他们的情况,南宋邕州官员吴儆《论邕州化外诸国状》和明代刘文征所撰《滇志》均有记述:自杞国人个子高,眼窝深,脸黑齿白,喜欢赤脚、戴笠、披毡子。腰间系着用芦苇织成的带子,手臂上带着金银打造的圆环佩饰,身上随时挎着长刀、弩弓、箭矢。乌蛮男子喜欢把头发扎起来,上面佩戴一些兽骨、飞禽的羽毛(像印第安人)。身上穿着用用兽毛、猪鬃、头发混合碾压揉成的毡子。骑的马没有马鞍,只有用木头剜成鱼口状仅能容下脚趾的马镫。妇女则耳朵上戴着大耳环,剪着齐眉刘海,穿着露出膝盖的布裙(这与东爨乌蛮的后裔彝族的服饰相类似)。氏族内部族规很严,部落酋长掌有生杀大权,即使是平常与自己关系很好的族人,如果违反了部落的规则,也会被杀头,所以境内无盗窃,家家户户柴扉大开,夜不闭户。但酋长经常率部众外出劫掠外族,抢得的财物一部分归战士,大部分归部落首领。
在生活习俗方面,南宋诗人范成大也多有记载。范成大是一个眼界开阔、感觉敏锐的文学家和旅行家,他一生游历了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许国无功浪著鞭,天教饱识汉山川”。对于殊方异域、奇风异俗,范成大有着强烈的兴趣。在游历到广西南宁、桂林时,他听闻了自杞国的奇风异俗,在文章中作了记录。在其所著《桂海虞衡志》中记载:自杞国人有“共饭一盘,用匕抄饭,抟之而食”的习俗。实际上,这样的习俗可以说是本地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对外来的汉民的影响,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仍然存在。我们小时候,几乎每个小孩都吃过“饭团子”,就是每次外出不能按时回家吃饭,父母就会把米饭捏成“饭团”给我们揣上,在外面肚子饿了,拿出来找个有火的地方烘烤热乎,就可以就着水啃着吃了。后来陆良出现了久负盛名的“陆良小粑粑”,推测与之也有着直接的关系。陆良小粑粑是将普通稻米或糯米煮熟,反复碓(石臼)舂至粘性很强后,抟成扁圆形的饭团,随身带上,专门供在野外不方便生火煮饭时食用。为打仗时部队士兵、打猎的猎人或翻山越岭的马帮所喜爱。后来因为时间一长,饭块会变馊,逐步改成用小麦、荞麦再加糖粉等原料做成。这种食品保质期在十天至半个月左右,而且最重要的是携带方便,取食时方便,只要有火、有水,根本不需要锅碗瓢盆就能食用,并能很快地填饱肚子,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压缩饼干”,比之后来北方军队所用的“炒面”、“小米”等等方便、实用多了,因而大受欢迎,很快就闻名遐迩,大名远传。这也是陆良本土先民聪明才智的具体体现。

《滇志》还记载乌蛮人的游戏:“腊月为春节,竖长杆,横设木,左右各一人,以互落为戏。”这种游戏方式在陆良一带一直流传至今,叫“打磨楸”。改革开放前十分盛行,每年春节,几乎每个生产队或街市人烟集中的地方,都要支起架子,搭起“磨楸”,供人们娱乐开心。分田到户后,也仍然有爱好者自发出资搭建,喜欢玩的年轻男女很多。而现在,“打磨楸”则成为民间文艺演出队舞台表演的保留节目,但场面却要惊险、有趣的多:一个精赤着上身的壮汉,肩负着一根长约四五米的粗木杆,木杆上则是两个甚至四个青年男女,做出各种欢愉、淘气、戏耍的动作、表情。壮汉既要负重,还要把木杆在左右两肩轮流倒换、旋转,表演难度之大、体力消耗之大,比起杂技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关自杞国的历史,最主要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贩卖战马开展的贸易经济;二是以防御为主开展的军事战争。
自北宋开始,北方蒙古、夏、辽、金不断南侵,大宋王朝节节败退,终于丢掉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在临安(杭州)建立南宋政权。过去,宋朝军队的战马主要来自于北方和蒙古、甘肃等地。由于北地尽失,军队所需的战马来源中断。为此,朝廷不得不寻求别的地方的马匹供给军队。此时,一直与宋朝一直有着良好关系的大理成为南宋朝廷获取战马的首选之地。大理马“善驰骤,能日行数百里”,而且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仍可以奔跑。实际上,早在北宋时期,金人占据黄河北岸后,朝廷即已从云南大理购买战马。北宋元丰年间,朝廷在广西邕州专设买马官,负责购买战马。南宋时期,由于北方战马来源完全中断,朝廷在邕州设立了专门的买马机构——提举买马司,配备专职买马的官员负责买马事宜。战马的交易场所主要设在邕州境内的横山寨和宜州(今广西田东县平马镇附近)。

自杞国本不产马,但大理马前往邕州,横亘于大理和南宋之间的自杞国是必经之地。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精明而又强悍的自杞国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条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于是,他们走上了从大理国贩马至邕州卖给南宋朝廷的“金光大道”。为了争夺马市交易,自杞国与周边罗殿国等部落甚至南宋军队还不断发生摩擦,沿途需有强悍的兵士护送,因此他们建造了无数的哨卡、战垒。一开始,自杞国所贩战马每年大约在1500匹左右,随后逐年增多,最多时每年有数千人前往横山寨,贩马5000多匹。在横山寨马市,他们贩卖的战马所占比例高达四分之三还多,几乎垄断了云南马的贩运和交易市场。自杞国至此确立了“贸易立国,贩马兴邦”的国策。通过战马贸易,自杞国迅速致富,势力已超出罗殿之上,独雄于诸蛮,一跃成为西南地区仅次于大理国的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强悍、骁勇、蛮横的自杞国武士,南宋朝廷对之无能为力(自顾不暇),大理国统治者也莫可奈何。
在贩马的同时,自杞国人还将云南的山珍奇货也带到了横山寨出售。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有“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药物、豹皮”等物品。其中特别是“长鸣鸡”非常有意思,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也记载:“长鸣鸡,自南诏诸蛮来。形矮而大,鸣声圆长,一鸣半刻,终日啼号不绝。蛮甚贵之,一鸡值银一两。”范成大认为这种“长鸣鸡”是因为叫声奇异且叫的时间比较长人们感觉好奇而喜爱,应当是南宋人买了去养着玩的宠物。一两银子买一只鸡,如此高的价格,总不会是买了回去杀了吃掉吧。实际上,这种长鸣鸡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功用,《滇志》记载:一是“司晨”,每天早上报时,用沙漏检测后发现十分准确;二是“善斗”,善于打架,可能曾被用做赌钱的斗鸡。
自杞国人在横山寨与南宋交易马匹,以金银现金交易为主,很多时候也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回自己国内缺少的梦寐以求的盐巴、锦缎、丝绸、布匹、瓷器等生活用品。交易时,南宋官员和自杞国首领双双坐在交易大厅庭上,喝着茶,聊着天,下面的具体办事人员则在庭下根据各匹马的高矮胖瘦讨价还价。南宋为此每年要支出数十万两白银和价值不菲的物资,这对于小小的自杞国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钱多了,自然财大气粗,说话口气也硬,称强于横山,日益骄横。有一年,自杞国一名酋长甚至“持其国书”到邕州与南宋地方官员交涉,要求他转交给朝廷,提出“请以乾贞”为年号,这实际上是要求南宋政府承认其独立地位。更为夸张的是酋长公然提出要与南宋皇帝“联姻”,效仿大唐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迎娶南宋的公主来做儿媳妇。这种过分的要求当然遭到了南宋的拒绝。

与此同时,在交易的过程中,双方因价格和其它原因也屡次发生冲突,宋与自杞双方均有所杀伤。以至于邕州官员不得不“傍引左右江兵丁会合弹压,买马官亲带甲士以临之,然后与之为市”。范成大记载说,自杞本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蛮人部落,却非常凶狠、狡猾,而且贪得无厌。在横山卖马,稍微不如意即拔刀伤人,甚至搞出命案。一旦出现杀人情况,邕州官员也采取杀同等数量的蛮人以平息双方的怒火。此即所谓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乃中国自古以来的伦理法则。邕州官员吴儆与自杞国首领庭上相见时,对自杞人严厉斥责并威胁说:朝廷允许你们每年来卖马交易,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你们每年获取财物超过二十万银两,你们国家因此得以致富,你们应该感到庆幸和满足。如果忘记了朝廷的厚恩,还强买强卖,变本加厉地提出过分的要求,我们也不会客气。如果你们再像这样蛮狠霸市,我们一定会申奏朝廷,从明年起就断绝和你们做生意。
自杞国建立军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保家卫国,抵抗外来侵略;二是保护、护送贩马队伍不受其它势力的侵扰。
自杞国拥有十分强悍的军队,这是因为他们有着特殊的训练战士的方法。
我们知道,江浙绍兴出产一种酒叫“女儿红”,是说哪家生了女儿那天,就将一坛或数坛酒窖起来,等到女孩长大成人出嫁时,拿出来招待亲朋好友,陈年佳酿,香醇醉人,甘之若饴,非常有名。绍兴人是为女儿成为嫁娘准备喜酒,自杞国人却是为男孩成为战士准备武器。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战斗和打猎是必要的经历,所以自杞国人特别重视男孩勇猛精神的培养。他们一方面让男孩从小就参加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各家若生下男孩,从出生之日开始,便将40斤铁投入炉火中烧炼、锤炼。以后每年锤炼数次,至小孩长到15岁成年,经过千锤百炼后的铁坨,到这时仅剩下七、八斤精铁,将之打造成长刀,镶上手把,成为小男子汉的随身兵器。这种刀钢火、韧性都极好,锋利至极,可吹毛断发。每年耕种、收获完了以后,自杞国人即开展大练兵活动。训练中不是用木刀、木枪,双方都是真刀实枪的对打、对砍。这种训练方式使自杞国人从小便获得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锻炼出了极强的战斗力。每有战事,各地成年男人即自带甲胄利刃武器,粮食一斗五,肉干若干,投入战斗。因为没有补给,自杞国战士担心粮食吃完了仗却打不完,都想早早地结束战斗,因而打起仗来都特别凶狠卖命,战斗力超强。每战几乎都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速战速决。自杞国还专门培养了一批称为“苴可”的敢死队员,骁勇善战,“喜斗轻死”。他们随身携带有劲弩、毒标、毒矢,“发其二必中二人”。在战斗中,凡面部、前胸受伤者,说明他是面向敌人冲锋所致,皆有嘉奖;凡是背部受伤和后退者,说明他是逃跑者,必遭斩杀或严惩。这样严格的奖惩制度和尚武精神,使自杞国人在打仗时勇猛无比,十分剽悍。
自杞国“有精骑十万”,平时为民,战时为军。他们的军队在蒙古人南侵时上演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勇抗元、保家卫国的悲壮之歌。
1253年秋,元世祖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率领十万蒙古铁骑,从宁夏六盘山出发,行程两千余里,过大渡河,跨革囊、皮筏渡过金沙江,迅速降服丽江、大理等地。随后,忽必烈返回北方,兀良合台率军继续南征。蒙古大军以大理军为前锋,向乌蛮三十七部进攻。大兵压境,自杞国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自蒙古军进攻善阐(昆明)开始,到蒙古军渡南盘江进攻南宋之间,自杞国坚持抗战长达五年之久。以国王那句为首的自杞国统帅们,制定了全民防御战略。又根据蒙古骑兵善于长驱驰骋、快速奔袭的特长,仿效北方长城构筑了一道滇东长城,作为战略防御之依托。随后,蒙古军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抵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伤亡。“盖以合刺章(蒙语:乌蛮)战士众多,防守甚力,逐日搏斗,蒙古军不久仅存二万人。”也就是说,蒙古军几乎损失了8万人。乌蛮战士以忠心和赤胆,以勇敢和无畏,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抗击着蒙古军队的猛烈进攻。在几乎每天都要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斗中,没有一个乌蛮战士投降。他们或正面抵御、抗击着敌人的马刀、火器;或凭借熟悉的地形,穿行在滇东幽深的山谷密林之中,机动灵活、神出鬼没地开展游击战,给擅长在开阔地奔驰砍杀的蒙古军队以重大创伤。由于没有外援和失去了经济来源,蒙古军队又施行了残忍的三光政策,自杞国国土一寸一寸的沦陷,山寨一个一个的被烧毁,城池一座一座的被夷平。至1258年秋天,自杞国的大部分国土被蒙古人占领,都城必罗笼被焚毁,“川谷为之一空”,自杞国人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被迫逃亡的国王及其部属人员退至兴义、罗平、师宗、泸西、丘北一带的深山老林和南盘江两岸继续抗战。1259年,兀良合台渡都泥江(南盘江)进攻南宋广西前线,国王那句还派人给南宋边关守将送去重要的军事情报。

自杞国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自杞国只存在了160余年,但它却创造了许多历史奇迹,留下了许多神奇的故事。对内,它创立了自成体系的、特色鲜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使国家迅速强大,人民安居乐业。对外,它占据地利之便,开展以贩卖战马为主的贸易经济,开拓了云南至广西的贸易通道,与内地互通有无、互为依存,突破了封闭的疆域和空间,也沟通了边疆文化和内地文化的交流。
但我以为最值得人们记住的自杞国的辉煌,是它在抗击蒙古大军时表现出来的勇猛顽强、不屈不饶的韧性,以及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保护南宋的屏障作用。蒙古大军席卷欧亚大陆,铁骑所至之处,所向披靡,势不可挡。但在南下吞并整个中国的征途上,遇到了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无法从正面突破。于是,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行程数万里路,绕道地广人稀的大西北,试图从南面进攻南宋。在轻松取得丽江、大理之后,本以为进攻南宋是指日可待的事,想不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处于大理国与南宋之间的自杞国,成为蒙古军队一路高歌猛进的绊脚石。忽必烈觉得,大名鼎鼎的大理国一夜之间尽皆臣服,其余诸蛮当不在话下,不值一哂。于是,他先行返回大都,留下兀良合台继续完成下面的征途,无非是一条毫无悬念的胜利之路,没什么可担心的。作为蒙古帝国的一员悍将,兀良合台曾征战图们江流域、波兰、捷克、匈牙利、德国等地,战功卓著。这次率军东征,他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唾手可得的大功劳和丰厚的封赏似乎就在眼前,已经向自己发出了微笑。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通过自杞国小小的国境,却是一段欲哭无泪的艰难征途:幽深神秘的山林河谷,神出鬼没的乌蛮士兵,莫名其妙的毒矢箭镞,从天而降的巨石滚木,以及饥饿、寒冷、瘴气、恐惧、死亡……不分白天黑夜地伴随着这支远道而来的疲乏的军队。当蒙古军队惯用的速战速决的闪电战失去效果后,兀良合台和他的儿子阿术不得不将征战的节奏放慢,一山一林地前进,一村一寨地夺取。正史记载,在此期间,阿术甚至多次亲自带领士兵攀援悬崖峭壁实施突袭。占领自杞国全境后,兀良合台又继续攻占了越南、贵州等地,始与南宋军队交战。虽连克数十城,破敌数十万,立下不世奇功,但忽必烈对他并不满意。忽必烈本来就因为他是蒙哥汗的重臣而对其“疑而忌之”,这次东征不但战事旷日持久,还损兵折将,大大的堕了帝国的威风。因此,兀良合台北上回京(大都)后,忽必烈不仅没有给他加官进爵,还立即解除了他的兵权,将其凉在一边。兀良合台作为一代名将,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在孤寂中郁郁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