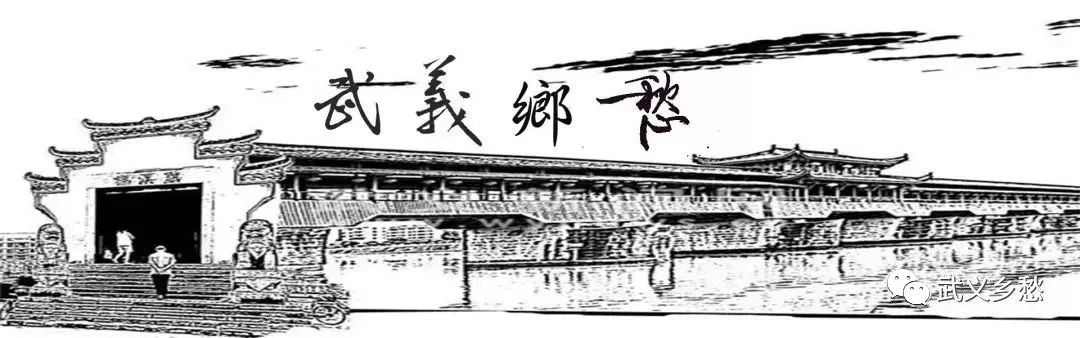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席慕容
光阴的故事
柳暗花茗
小时候总爱缠着大人讲故事,母亲不擅讲古,来来回回那几个烂熟的猜谜,她谜面还没讲完,我们便已报出谜底,很觉无趣。母亲讪讪,说:没空了,干活去咯!于是,我们跑去找太奶奶。
太奶奶总是讲太公公:“天一亮就起床,晚上天黑了才收工回家,一粒豆豉能送下一碗稀饭……”,我没见过太公公,总是在脑海里描绘着他的样子,太奶奶说他30多岁就走了,可关于他的故事太奶奶一辈子也没讲完。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已人到中年,太奶奶早已带着她的故事离我而去,而我也成了个爱讲故事的人。
是的,我总是想讲点什么,因为老家的房子要拆建了,我是多么的不舍。这个曾经的四合院,承载过我们家四世同堂的难忘岁月,住过和睦相处的左邻右舍,更有过和我一起长大的童年伙伴,如今人去楼空,满院疮痍。透过残存的窗棂,我依稀看见了曾经主人的脸,往事鲜活。
少年阿峰
阿峰是我邻居,两家房子相连,中间隔个走廊。他有个很风趣又喜舞文弄墨的父亲,这在乡下就显得与别家不一样,连带着阿峰也和我们这些小伙伴不一样了。他有一双非常明亮秀气的大眼睛,睫毛长长的,忽闪忽闪着,显得特聪慧。他小我一岁,却和我同时上了小学,课堂里,总能见到他奇思妙想的发言。
那时候,我特别不会削铅笔,怕小刀伤了自己。阿峰说,让我来,我可以不用刀就帮你削好。我好奇地跟着进他家,只见他把铅笔往一个木匠用的刨子上拉了几下,铅笔就削好了。他递给我,笑嘻嘻地说:“快不快?”

夏天热,那时候没有电风扇,阿峰会过来叫我:来我家吹风,保你凉快!只见他家门框上吊着一个草编的大帘子,上面系着一条长绳,地底下铺着一张凉席,他那个爱写作的父亲正躺着休息呢。阿峰说:你看住,我准备扇风了!只见他拉动那条长绳,大帘子马上一前一后摆动起来,刮起了大风,果然凉快的。阿峰开心地笑。
过年了,院子里家家户户要杀猪,今天你家,明天我家,大人们搭班子互相帮忙,整个杀猪过程都是体力活,在天井里追着猪跑,捆绑,上架,挣扎着的肥猪发出一阵阵凛冽的叫声。这个时候,大人们总是对我们说:去,躲一旁去,不准看!等着吃“猪三福”吧。
那天,阿峰跑到天井去了,他满眼含泪,大声喊:“不要杀,不要杀呀!”他抱着父亲的腿,拉住屠夫的袖子,哭着说:我不吃猪肉了,不要杀它,不要杀它。
大人们哄堂大笑。
不久,阿峰全家都去城里住了,与他做邻居也到此结束。仔细想来,我俩做同学只有一年时间,好像也没有正式告过别,至今,也没再见过面。
他家的房子还在,破败不堪。黑暗潮湿的走廊里,少年阿峰缓缓走来,嘻嘻笑着,一身晴朗。
阿南和他的媳妇
阿南哥住我家对面,他长我多岁,我上小学时,他要结婚了。新娘子是我外公那个村子里的,拿我母亲的话说,是同一个娘家的,因此我自然对她多了留意。
新娘子未过门时来看“人家”,她第一次上门,怯怯的。我仗着邻居,仗着和阿南的妹妹是“同年”,是一起玩的小伙伴,便不断出现在她眼前,故意发出声来引她注意。她果然不断地朝我看,没说话,脸蛋红红的。我很清楚地记着,她脸上长了些雀斑,但个子高挑,肤色健康,看着很舒服的一个人。
不久便是办婚宴了,大家都去闹新娘,最重要的环节是讨喜糖吃。我不顾新娘子处于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中,跟着众人喊“新娘子,发喜糖!发喜糖!”很奇怪,只要我一开口,新娘子总会冲破层层阻力把喜糖塞到我手里,几次以后,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换成别家,讨一颗喜糖有多难呀,几十人抢呢。
我望向新娘子,她对我微微一笑。
婚后,新媳妇和阿南特别恩爱,他们总是有说有笑,出入成双成对,田间地头里总有他们一起干活的影子。后来,他们有了孩子,新媳妇也不改习惯,经常抱着孩子陪在旁边。阿南性格很好,成天乐呵呵。
那年夏季,阿南哥背着锄头走在前面,媳妇抱着孩子跟着,突然间,打雷了,下大雨了。阿南回头看着媳妇,刚想说话,一道闪电从阿南身上劈过,阿南大喊一声倒地……他被雷击中了,因为肩上的锄头导电而至。
阿南走了,我的憨厚善良的邻居哥哥。
新媳妇不会笑了。后来的后来,她带着孩子离开了。
院子里从此没有了他们,他们的房子经历过火烧后又坍塌,如今只剩下一堵石墙和它脚下的一堆瓦砾。我知道,那斑驳的老墙里写着他俩的故事,岁月无语,时光尔尔。

江子的故事
江子也是我邻居,比我父亲年轻几岁,印象里皮肤黝黑,生性却好折腾。
他从小就经常走南闯北,要么学手艺,要么做点小生意,不甘做一辈子的穷人,但他屡战屡败,始终未做成一件事。家里只有一双父母,成天为他操碎了心,隔三差五替他收拾烂尾,更担心他娶不上媳妇。江子听不得父母的唠叨,一生气总是离家出走。
有一年,江子家可热闹了,涌来了很多人,他们来自周边十里八乡,拿着篮子、口袋,甚至挑着大箩筐的,村里喇叭正播着江子热情洋溢的声音:种植“洋姑娘”,发家致富好门路!据说,他也去镇里广播了,吸引着很多人来到他家,想看看“洋姑娘”是什么东西。有人以为是大件,所以必须拿箩筐挑回去。江子说,这是一种水果,好吃且营养价值高,易种植,当年就有收获,能卖好价钱呢。
人们虽然将信将疑,但也兴奋不已,陆陆续续掏钱买下江子的一包种子,“洋姑娘”的种子。那时候,农村刚刚分田到户,被割了几次“资本主义尾巴”的江子认为他创业的时代来了,广大农民也摩拳擦掌准备种经济作物,搞副业,争取做“万元户”,江子更是信心满满。
半年后,“洋姑娘”种植有结果了,曾经的那些人又跑到江子家来,这回是来骂人的,说江子是大骗子。

原来,“洋姑娘”就是田间地头常见的灯笼果,金黄色,小小个的,类似小番茄。当时大家都以为是大气的上档次的水果,至少应该像苹果一样的外表嘛!江子傻眼了,他也解释不清,只好脚底一抹又离家出走了。
其实,“洋姑娘”盛产于东北,也叫“大姑娘”,酸酸甜甜的,确实营养丰富,只不过它的价值在很多年后才被人认可。
又过了一阵子,江子打道回府,这次他带回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一起来的还有一群小姑娘,来自宣平山区。更重要的是请来一个上海师傅,说是要办厂做手工编织的地毯、挂毯,产品在国外很受欢迎的,卖得高价。
他租下我们院子里的一个大厅做厂子,姑娘们白天织毯子,晚上就打通铺睡在大厅。上海师傅是贵客,需单独安排间房子给她住。江子家没有多余的房子,于是求到我父亲,父亲便把我家二楼一间最好的房子给师傅住。
我已经上中学,周末回家能看到家里住着一女师傅,大厅里一群姑娘,木制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幅有着漂亮花纹的毯子。
后来,听说毯子质量不合格,再后来,师傅走了,姑娘们走了,江子带着老婆也走了。
江子又失败了。
江子的父亲老实巴交,他唉声叹气,但不骂江子。不久,他生病了,日益消瘦,最终在医院病逝。江子红了眼睛,他依然没有致富,没能衣锦还乡,没能光宗耀祖。
又过了几年,江子回来了,他西装革履,拎着酒和点心来看我父亲。他说他在杭州,在郊区租了些地来种菜,然后运到市区去卖,因为菜品非常新鲜,生意很不错。他眉飞色舞,说接下来要扩大种植,市区卖菜的档口也要多设几家。他知道,他想象中的日子要来了。
然而,世事无常,回杭州不久,噩耗传来,江子在运输蔬菜的路上出车祸,他丢下母亲,老婆,幼子,撒手人寰了……
是我父亲去的杭州,携他的妻儿把他的骨灰送回来。江子的母亲嚎啕大哭。
江子的老婆带着儿子继续在杭州继承着丈夫的事业,即使后来改嫁了她依然赡养着江子的母亲,直至老人去世。
江子家的房子随着他母亲的去世是越来越残旧了,青砖灰瓦,窗棂楼阁,落满了时光的尘埃。
它们静默无语,它们一动不动,我的内心已是沧海桑田。
庭院里爬满青苔,光阴里盛满故事。

注: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