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样的食物,你可以看到它的脚步在世界的范围内行走,每走到一个地方就会生发出新的变化来。”
——《落地生根》导演邓洁
在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随便走进一间茶室、美食中心,都可能会邂逅令人惊艳的海南鸡饭。
做海南鸡饭要先处理鸡肉。汆烫鸡肉的锅里,表层飘着的那层油花就是鸡饭美味的精髓。撇起鸡油,大火热锅,将生米撒下,就着干葱叮叮咚咚地快速翻炒出香气。这还没完,要用刚刚烫鸡的汤替代水来煮饭,一只鸡齐齐整整地被运用在料理的各个环节,才算是真正物尽其用。

▲ 鸡汤煮饭
* 《风味人间》
如此煮出来的鸡饭,米粒上带着一层饱满的油光,散而不粘,粒粒分明。入口时既有鸡汤的鲜美,也潜藏着先前烫鸡时加入的姜和香兰叶的复杂风味。不用配菜,就能轻轻松松扒掉大半碗。
不过没人能抵住鸡肉的诱惑,空口吃饭。一小盘斩件的海南鸡,垫着黄瓜片端上桌。

▲ 海南鸡饭粒
* 《风味人间》
一只优秀的海南鸡,应当是皮肉相连,油光锃亮,骨头旁边还微微带一点桃红色,是一条将凝未凝的细血丝。因为汆烫的过程中多次起锅,又沁了冰水,鸡肉紧实,软嫩多汁。利索地夹起一块鸡肉,蘸点料吧——咸中带甜的黑酱油、用鱼露调成的辣椒酱,又酸又辣又鲜,几种味道达到了极致的平衡,一口咬下去,肥美不腻,又充满韧性,只觉得人生至此圆满。

▲ 蘸点料吧
* 《风味人间》
海南鸡饭,其实正是一个关于迁徙与承袭的故事。
有一些食物,随着移民的脚步不断在地理空间上延展,跑马圈地的过程中却时时不忘承袭,在风雨飘摇中尽可能地保持着原始样貌,比如流传于马来西亚的传统中国菜。
有一些食物,则跟着人一路走来,而移民在迁徙的过程中随手又拾起各种各样的新食材,最终新旧各种食材、做法汇聚在一起,完成了饮食的再创,比如马来西亚本地化的中华料理。

▲马来西亚的海南会馆
* 《风味人间》
海南鸡饭无疑是前者,它是19世纪移居南洋的海南移民,对海南原乡祭祖风俗的重现。
祭祖要用文昌鸡,这是海南岛上节庆宴席、酬神祭祖都必不可少的一道传统菜式。而农村家庭在杀鸡还神之际,常用余下的鸡油鸡汤来煮米饭,再将做好的鸡饭捏成饭团,祈望圆满丰富、阖家团圆。这些乒乓球大小、白白胖胖的饭团子,被海南文昌人称为“饭珍”。

▲祭祖的文昌鸡和 “饭珍”
* 《风味人间》
现在的海南,把鸡饭做成饭团的风俗已经很少见,在餐馆里点文昌鸡,端上桌来的可能就只是一份白斩鸡而已。但鸡肉与鸡饭的固定搭配,却在新马一带保留了下来。
当年的海南人,作为几乎最晚到达的移民,可以选择的工作已经不多,于是很多人不得不用从家乡承袭下来的手艺谋生。在马六甲,在槟城,在新加坡,他们挑着扁担走街串巷,一头的竹箩里装着白切鸡,另一头是香蕉叶包裹的鸡饭。这,就是最初的海南鸡饭。
几十年的发展,让海南鸡饭在南洋遍地开花,成为最便宜美味的一人食典范。但只有在马六甲,才能吃到鸡饭粒。
一颗颗圆滚滚的饭团,排放整齐地呈上来,表面光润绵软,一口咬下去,内里的饭粒却松软而充盈着颗粒感。再夹起一块滑嫩带皮的鸡肉,蘸上酸柑打底的辣椒酱——这就是鸡饭粒,它和海南鸡饭唯一的差别,是保留了把鸡饭紧紧地揉合成球形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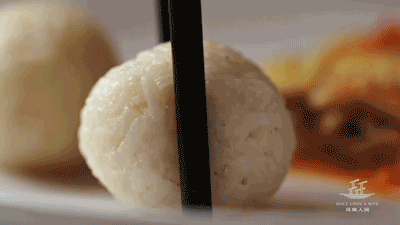
▲饭粒松软而充盈着颗粒感
* 《风味人间》
为什么是饭团?
不论地域,所有追溯海南鸡饭历程的文章,都会给出自己版本的解释。有的说是最初流动摊贩售卖,捏成饭团鸡饭的香气和热度不易散失;有的说最初海南鸡饭的消费对象多为劳工,捏成饭团易于他们取用。
今人或许可以从实用的角度考证,给出无数种捏制饭团的原因。但将时间倒转,问问那些初到南洋、辛劳地沿街叫卖鸡饭的海南先辈,或许就是最下意识的,对祭祖酬神时饭珍的复刻而已。故园已然万里相隔,过去宗族相聚祭祖、共食饭珍的回忆却格外清晰。于是鸡饭自然而然地被捏成了饭珍,堆叠在竹箩中氤氲着热气。

* 《风味人间》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南鸡饭在南洋不同的地方行走、流变。甚至在海南岛上,都随着时间流逝而起伏变化。飘摇零落,迁徙中却总有一些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如今在马来西亚华人中,仍可以看到以鸡饭粒祭祖的场景。于是鸡饭成了媒介,是整个宗族、上溯几十代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共同的记忆。
拿取一只饭珍,触手微温的,是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