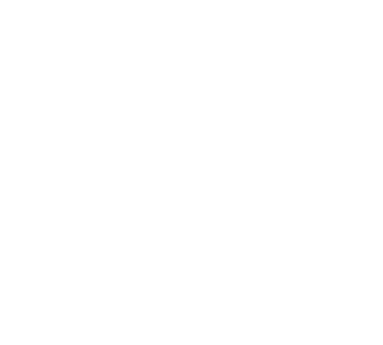长江禁渔迈入了第四个年头。禁渔“成绩单”怎么样,退捕渔民的“新生活”如意吗,新阶段要关注什么新问题……记者多方走访,试图拉直长江禁渔的六个问号。
01
一问:2024年是长江十年禁渔的第四年,目前有哪些“看得见”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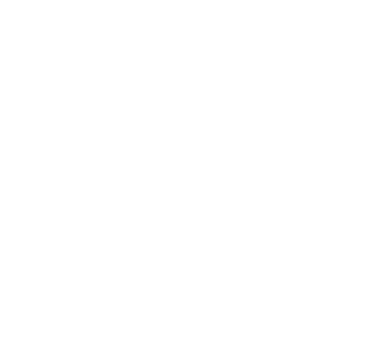
春潮迷雾出刀鱼。曾经,每每清明时节,长江刀鱼上市前后,关于它的话题便在申城大街小巷热起来,而“价格涨没涨”尤其受到关注。
据记载,刀鱼年产量曾高达4000多吨。到了20世纪90年代,年产也有1000多吨。而在禁捕前夕,年产量下降到60多吨。渔汛缩短到只有三五天,捕上来的刀鱼越来越小。
“每年科研人员都能采到样本。2018年至2020年,监测到的刀鱼平均个体体长不足10厘米,平均体重不到5克。”长江口水生生物资源监测与保护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长江口联合实验室”)秘书长韩东燕给出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
当生活不再因为“绝户网”戛然而止,刀鱼开始“胖”起来——2021年至2022年的监测数据显示,刀鱼的平均体长突破10厘米,体重也翻了一倍。而最新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也点出,四大家鱼、刀鱼等资源恢复明显,刀鱼能够溯河洄游至历史最远水域洞庭湖……

资料图:2023年2月,松江区多部门开展黄浦江松江段渔政同步执法巡查行动,确保禁渔工作落到实处 新民晚报记者 陶磊 摄
当然,对于刀鱼的“回归”,人们可能是不知道的。但有“食客”感受得到——长江江豚。
“现在在长江里看到江豚,不是那么稀奇了。”韩东燕感叹。作为长江水生生物食物链顶端的存在,江豚是长江生态环境质量的“晴雨表”。长江江豚的数量曾急剧下降,2017年跌至谷底,约1012头。十年禁渔后,江豚的口粮多了,也不会陷入“天罗地网”无法脱身。最新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1249头。这是自2006年有监测记录以来的首次止跌回升。
“禁渔后的两年内,长江口水域累计监测长江江豚35头次,较禁渔前有较大提升。”韩东燕告诉记者,“单次目击最大种群数量8头,较禁渔前增加33%。”相比于看到江豚次数更多,专家们普遍对单次8头更加激动——这说明有宝宝降临了,家族壮大了!
“过去,我们科学考察一个航次只能发现两三尾东方鲀,禁渔后随机一个监测站就能发现六七尾,而且个头也变大了。鲈鱼等出现的数量也明显高于禁渔前的监测数据。”韩东燕欣喜地介绍。

2022年8月,长江江豚在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坝下游大江水域逐浪嬉戏。来源:东方IC
02
二问:都说“长江禁渔看长江口”,上海所处的长江口缘何那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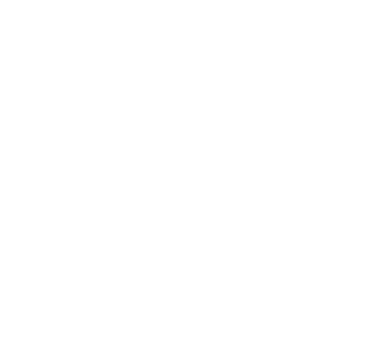
“长江口,是能为长江坐诊把脉的地方。”长江口联合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潘迎捷教授开门见山。
绵延6300多公里的长江,从江苏镇江开始,便进入了三角洲河段。而在江阴以下的河口段,江面不断扩张成喇叭状。从北面的启东嘴到南面的南汇嘴,长江口的宽度达91千米。由江水带来的泥沙进入河口区,经咸淡水交接汇合,发生絮凝作用并引起下沉,于是,又孕育了诸多沙洲。
在长江口,中华绒螯蟹和银鱼在此地产卵繁衍;中华鲟幼鲟、刀鱼和凤尾鱼在这里索饵成长。因此,长江口就是产卵场、索饵场、育幼场,亦是中华鲟等洄游性鱼类的必经通道。
“长江口对于生态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对河口主要渔业资源和保护动物的生态功能。”潘迎捷分析,长江口的生态一旦失衡,就像是扼住了这些重要渔业资源和保护动物繁衍生息的咽喉。
在老一辈渔民的记忆里,长江口曾有过“五大渔汛”:凤尾鱼、刀鱼、前额银鱼、白虾和中华绒螯蟹。时过境迁,“忽惊网重力难牵,打得长鱼满船喜”只能停留在回忆和传说中了。更令人心痛的是,长江口的生物多样性明显退化,濒危水生动物逐年增多。
“保护长江口的渔业资源,修复治理长江口的生态环境,刻不容缓。”潘迎捷指出,长江口联合实验室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21年春天成立。
韩东燕补充说,实验室成立至今,完成了8个季度的水生生物资源监测任务,包括长江口全水域40余个监测站位,共组织出航60余次,已完成了2万余尾的水生生物监测数据报备,“实验室还研发了具备鱼探仪功能的小型监测浮标,解决了24小时不间断监测生物资源量的问题”。
03
三问:渔民退捕,离船上岸转变生产方式后,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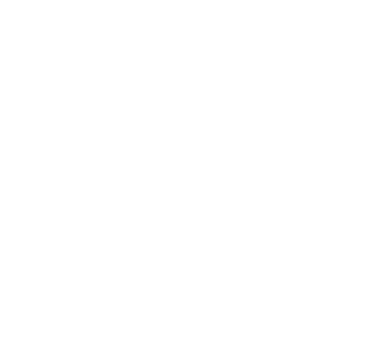
“长江禁渔,要有将心比心地帮扶!”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廷贵教授如是说。十年禁渔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只有解决好渔民上岸后的生产生活问题,禁渔才有稳定、扎实的社会基础。
长江禁渔实施后,为确保渔民退捕后的生产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十省百县千户”长江退捕渔民跟踪调研实施方案》。“长江流域建档立卡的退捕渔民共计23.1万。我们从中选取十个省、每省再选取十个县,并根据性别、年龄、专业等在每县抽取渔民,开展为期十年的跟踪调研。当前在跟踪调研系统的退捕渔民为3881名。”陈廷贵介绍。
很多上海市民听过“刀鱼王”彭海兵的故事。1972年出生的崇明汉子20岁就开始和人合伙做贩刀鱼的生意,后来又自己买船、造船,出去捕捞,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手下有四五十条捕鱼船。前几年他放弃了刀鱼生意,转而成立了“鲟豚使者联盟”志愿组织,变身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志愿者,还协助科研人员开展项目。

资料图:渔民上岸后变身护渔员。新民晚报记者 徐程 摄
显然,不可能所有渔民的转型都能那么顺当。“渔民心里也都有杆秤。”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院长唐议教授说,“目前来看渔民基本做到了‘退得出、稳得住’,可离‘能致富’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中央和地方累计落实禁捕退捕补偿补助资金272.31亿元;沿江约16万名有就业能力和就业需求的退捕渔民转产就业;约22万名符合参保条件的退捕渔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2021年来,上海海洋大学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西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组建团队,利用暑假对跟踪调研系统中的3881名退捕渔民入户调研。“这些渔民来自121个县550多个乡镇,其中灵活就业26.1%,企业吸纳22.2%,公益岗位安置17%,自主创业17.8%……月平均收入3900元。”陈廷贵给出一组数据。
陈廷贵指出,尽管就业率可观,但部分退捕渔民仍面临就业质量不高、经济收入增长缓慢等现实,“有些渔民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缺乏除捕鱼之外的其他就业经验和技能。尽管地方政府花大力气开展再就业培训、组织招聘活动,但适合他们的岗位仍然有限。”
不过有一点,陈廷贵感触良多。在入户调研过程中,他对100多位受访渔民提出了同一个问题:还愿意让下一代从事捕鱼吗?没有一个人说愿意。有个上小学的“渔二代”告诉他,大夏天再也不用穿这防水衣了,现在坐在教室里,很开心。
“这是长江十年禁渔‘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生动注脚。”他感叹。
04
四问:长江禁渔“三年强基础”后,当前最紧迫的关注点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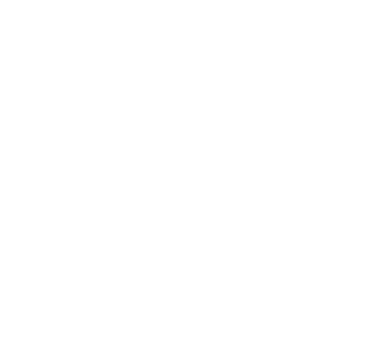
“中华鲟!”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后,几乎所有专家不约而同说出了这个答案。更准确来说,是以中华鲟为代表的长江珍稀鱼类。
长江里的“双白”——白鲟和白鱀豚,已经永远甩开了人类,游入了最深最深的湮灭之河。每每这样的消息传出,万千网友无不表达着痛心和惋惜,“我们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
在渔民代代相传的谚语中,就有“千斤腊子(中华鲟)万斤象(白鲟)”一说,而“灭绝”的结局,似乎像一个黑洞,正拉着中华鲟坠入无尽深渊。“科研人员已经连续五六年没有发现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了。”上海海洋大学鱼类研究室主任唐文乔教授严肃地指出。

资料图:2021年末,上海科技馆主办“大江行地”长江主题科普展,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鲟、中华鲟等珍稀鱼类模型亮相。
唐文乔介绍,中华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多年维持在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物种名录的“极危”等级,“对于水生生物的保护,仅靠禁渔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像中华鲟这样的河海洄游性鱼类,它的栖息地、产卵场、育幼场的修复,对于物种的保护都不可或缺。”
记者了解到,葛洲坝上游曾有600多公里、20多处的中华鲟产卵场,它们每年会在众多“产房”里选择最合适的。葛洲坝修建后,中华鲟无法上溯,不得不屈居坝下约4公里,不到1平方公里的区域产卵,“多选题”陡然变成“是非题”。三峡工程蓄水后,让长江的水文、水温节律发生改变,进一步冲击中华鲟的自然繁殖。“到了产卵时间,‘产房’达不到标准,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华鲟的性腺退化。”唐文乔解释。
长江口联合实验室的监测证实了大家的担忧,“2021年首次未监测到中华鲟;2022年监测到6尾中华鲟,均是带有标记的长江上游增殖放流个体。”潘迎捷告诉记者。
同样不容乐观的还有申城市民颇为熟悉的,有中国四大名鱼之称的松江鲈。监测发现的松江鲈多出现在二三月,平均体长117毫米平均体重26克,推测为增殖放流个体,目前已多年未见自然繁殖。

2020年全国“放鱼日”,上海长江大桥北岸东侧海警码头水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新民晚报记者 刘歆 摄
“保护长江珍稀物种的力量和速度,要和它们的灭绝速度赛跑。科学家如果跑不赢的话,物种就灭绝了。”潘迎捷坦言。
更多人正全速跑着。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正将生殖干细胞繁育技术用于中华鲟的繁殖研究,以期扩大种群。同时,上海持续多年开展了珍稀濒危水生动物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放流中华鲟、松江鲈、胭脂鱼等珍稀、珍贵物种85万余尾,底播底栖生物300余吨。
05
五问:禁渔好比是给长江“治病”的重要举措。临床上,医生会根据病症动态调整治疗方案。十年是一个较长的跨度,是否需要补充或科学调整举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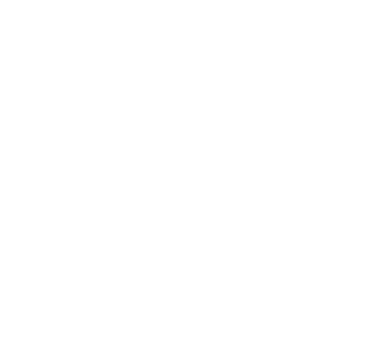
十年禁渔是一场持久战。冲刺“一年起好步、管得住”,迈过“三年强基础、顶得住”,步入“十年练内功、稳得住”的新阶段,也面临着长江“初愈”后“治疗方案”的科学研判。
“禁渔不是禁鱼。长江传统捕捞业的业态是不可持续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潘迎捷指出,然而长江鱼类资源,尤其是经济鱼类的科学合理利用是可以有序发展的。在他看来,在“练内功、稳得住”的新阶段,两个问题绕不开:如何更有利渔业资源的保护;如何合理利用渔业资源,特别是那些人放天养的生态型优质鱼类蛋白。
唐议解释,鱼水相依,鱼少了水草疯长,水质恶化;反之,鱼多了,水生态失衡,水质同样恶化。过去,一些封闭湖库,每年都会增殖放流,也会回捕相应数量,维持水生态环境。十年禁捕后,放流照旧,捕捞不再。湖泊草食性鱼类过快增长,沉水植被遭遇破坏,湖泊降解污染能力反而降低了。
记者了解到,湖北省5个湖库曾于2022年开展生态捕捞试点工作,生态捕捞实行“一湖一策”,有严格红线。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捕捞仅涉及禁捕保护区中的小部分湖库,长江干流、支流依然实施最严格的禁捕政策。
“十年禁渔是调整优化渔业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的重大机会窗口。”唐议说,十年禁渔期满后如果开放捕捞也会和过去不同,应是组织化的行为、生态型方式,捕捞总量实行配额管理。通过生态捕捞,或有利于湖泊水质好转,同时将生态优势转化成为生态渔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
“不过,这同样需要科学分析渔业资源动态变化,总结生态风险管控长效机制的经验。”唐议补充道,“禁渔后,湖泊的水质生态先好起来,长江支流次之,干流恢复最慢。那么对于鱼类资源的管理,就可以‘反其道’,这是禁渔带来的启示。”
值得关注的是,非法捕捞呈现新特点,尤其是非法捕捞手段由“电、毒、炸”等传统方法逐渐转向新型禁用渔具、钓具。一些新型禁用渔具更易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获得,给执法部门带来了较大挑战。“近年来,垂钓产业蓬勃发展,钓竿、钓线、钓钩、钓饵各有市场。可部分休闲垂钓却‘变了味’,一人几十杆,一杆好几根线,变成了捕捞性钓鱼。”潘迎捷指出。
在潘迎捷看来,界定休闲垂钓和捕鱼并不容易,而且垂钓者们也更多选择监管“盲区”的偏僻天然水域,“禁渔的监管不仅涉及渔业部门,还有公安和市场监管等。要打破‘九龙治水’的流域保护常规做法,各管理部门形成合力,并与时俱进更加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