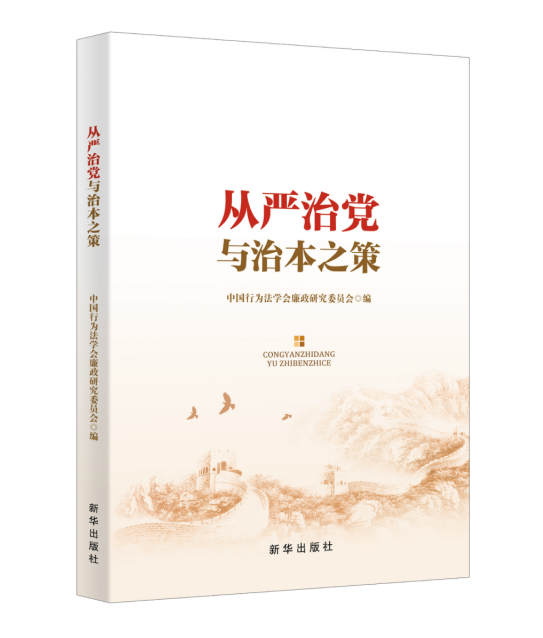□鄞珊
每一个潮汕人不管被扔到哪个角落,都会被牵扯到潮汕菜,都会被询问吃海鲜的事。好在现在四通八达,海鲜可以抵达任何地方,特别是诸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海鲜还挺多的。它们可以通过航空高铁等,科技完全可以保证海鲜们的颜色如初。
说到潮州菜,现今的名词,潮州的标签多被改为“潮汕”,或许只有这潮州菜可以坚挺地坚持“潮州”这个词。实际上,人们的理念基本以“潮州”名词覆盖潮汕地域。曾经在北京听当地人说,一条鱼死了十天,在北京就算是新鲜的了。我就很自豪,为自己作为潮汕人保持天天吃新鲜的海产品而幸福不已。特别是曾经一位年长的园林保管员听说我是广东汕头的,露出不无羡慕的神色问:“你们是不是天天吃海鲜?”得知我们真的天天吃海鲜,他几乎感到不可思议。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那些日子,我确实很难闻到鱼腥味,更别说看到海鲜的影子。交通的速度也决定着海鲜的“脚”。当地人告诉我,咱是不敢奢望吃海鲜,你说,几百块钱的工资,哪吃得起呀?至此,我才感叹自己多年来“身在福中不知福”,平时常吃没有感觉,几天没吃,我血液里的“海盗”开始出来作祟。那应该是猫缺乏鱼腥的本能,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去买鱼。不管是什么鱼,只要是海里的鱼就行——在沿海人民的心目中淡水鱼根本不能算鱼。
没有海的味道,怎能算是鱼类呢?!
说起来,我们家里一半人在海边生活,祖母那边更是世世代代的渔民。而我的吃鱼习惯却是受母亲的影响。想来这海边地方,谁家不是跟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家里却是不可一顿无鱼。没钱时买杂鱼小鱼,有钱时买好鱼——贵的鱼。弄得在那个缺荤少油的时代,我们也都不喜欢吃肉,偶尔买一斤肉,一家子十来口竟然可以吃上好几天。
我家的三亲四戚大部分是天天与大海拥吻的居民——我勉强找出“居民”一词,因为生活在海边,却不打鱼,严格来说不能称为“渔民”,以从事船员的工作居多。这也是可以拥有谈资的,也算是真正向大海讨过生活的,家人对吃海鲜都有一套臻熟的见解。走国际货轮、一生都在海上漂荡的船员姑父告诉我:海鱼不管高档低档,还是贵和贱,只要新鲜就是上品。真是至理名言!
姑父到过好望角,到过澳大利亚,到过日本,到过加拿大等国,漂过大半个地球,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对于海里的“居民”他最清楚。从大海的深处回到陆地,他可以藐视任何我们崇拜的鱼的贵族。我们捧为上品的金鲳、白鲳、鲍鱼,他连眼皮也懒得抬,却叮嘱我们只买鲜的就行,即使是剥皮鱼巴浪鱼也是好货。
被姑父点名的这些沿海里泛滥的鱼,上得岸来是非常便宜的,大凡口袋里还有点钱,绝对不会买它来招待客人。姑父反转了我们的惯性和理念,把我们那点可怜的虚荣心给擦掉。经济拮据的时候,我妈不好意思买薄壳,怕被人家笑话,却指使我去买,我一个小孩子不怕笑话,但我心里面知道来自薄壳的便宜和低贱。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便宜海鲜都具有其不可抵挡的美味。薄壳爆炒鱼腥菜,那是香飘一条街,虽然家家户户都加了一盘,却是买其它鱼之外的附带;同样便宜的剥皮鱼,焖生姜豆豉加葱,也是极品的美味。时间流转三十年,我才正儿八经地尝到这些渔获上到餐馆的菜谱,却昂贵得匹配不了它们的身份,何况味道还差了个十万八千里。
在市场上,我很少挑那些名贵的海鲜,只买很普通大众化的时令货,但必须有一双慧眼看出它拥有的新鲜度。很多内地人诧异:海鲜也要对应时令吗?当然有啊!六月的鲥鱼,秋天的螃蟹,它们都是对应季节的,应季的海鲜肥美好吃。走的地方多了,也知道规律,贵和便宜,有时仅仅是地域的差异。贵的东西,有时是因为稀罕,它在某些地方因为多到泛滥,恰恰就很低廉。时间和地理位置让它的价格发生倒置。
潮汕本土很贵的黄鱼——某一时期几乎是菜市场上最贵的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小一点的黄鱼一斤十多块,稍微大一点的,就要二三十来块。善吃的潮汕人认为黄鱼的肉质细腻,口感嫩滑,当属上品。外省的友人却告诉我,这种黄鱼在江浙一带特别多,且个头又很大,他们经常买来晒成鱼干——晒鱼干的都是特别便宜的,鱼头才几毛钱一斤,他们天天煲汤吃,都吃腻了,听得我们目瞪口呆:原来黄鱼换个地方也就是巴浪鱼的档次。
母亲常常叨念她小时候吃龙虾,那是因为外婆家没饭吃,连红薯都没有。这是真实的存在。那时外公利用便利,每次趁渔船靠岸,渔民分拣海产品,他就捡渔民们扔掉的龙虾,晒干。一布袋一布袋让我母亲扛回家当粮食,在没饭吃的时候用龙虾充饥。听起来挺荒谬,难怪母亲每次都轻蔑地说:龙虾有什么好吃?竟然那么贵!龙虾的肉质很粗糙,壳又硬,在以前都是渔民丢弃的东西,没人要。
从小在海边渔村长大的同学也经常诉说她在人之初时吃过的海马数量,她也是拿它当粮食吃。那才是真正缺衣少食,海马不比龙虾,除了一身铠甲,一点肉都没有。海马像刺一样,容易钩缠渔网。当渔民在沙滩上把海马、海参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扔掉时,那些没饭吃的孩子们就去捡拾,他们就地烧开柴火,把这些渔民扔掉的海产烧烤。倒是香喷喷的。多年之后回味,海边并不真正存在饥饿,大海的馈赠是丰饶的。
折转回来,现今的海马一斤几千块钱呢!据说补肾。
夏天大行其道的剥皮鱼,在市场上最便宜,当黄鱼三十多块钱一斤的时候,它一斤才两块钱到三块钱之间,买得我都很不好意思:真不是挑它的便宜,谁能体会它美味的精髓呢?它的好吃体现在骨头上,鱼骨是松软的,吃的时候不用剔开鱼肉,直接半截鱼就往嘴里送,“吧嗒吧嗒”地嚼,非常带劲。
后来它身价突然大增,十几块钱一斤,物价这东西很奇怪,一上去就只有继续上。这鱼也跟着跳龙门,我见它的价格一路狂飙。活的剥皮鱼,可以六十块钱一斤。而此时菜市场的黄鱼也只是十块钱左右,价格竟然委身其下,而后几年,这活蹦乱跳的剥皮鱼竟然追至每斤一百多元。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据说因为黄鱼价格昂贵,所以人们就开始搞人工养殖。在这个什么都可以“人工养殖”的社会里,野生的剥皮鱼凸显得“出类拔萃”了。
正因为如此,潮汕大地反其道而行之,时尚带动了吃法,人们喜欢吃“鱼仔”了——以前是家里的猫才吃。先是各种“鱼仔”海鲜店在海边春风十里地盛开,然后是家家户户盛行煲鱼仔汤,美其名曰营养汤。这倒是,当营养数据赫然见于报纸健康栏目时,我后悔自己懂的知识滞后了:曾经的营养都被家里几代的猫给带走了。
现在集市上的鱼仔是最先卖完的货,当从大海捞上来的新鲜鱼仔泛着亮晶晶的光,你会不由得被它吸引,腥气和星光一般生猛,越是细小越是带着原始的节奏。鱼仔堆里一般都是杂七杂八的鱼,小且不够名贵,还够不上分类。鱼贩干脆堆起一个小山堆,按斤称。每个买鱼的要不买它个三几斤以上都不好意思叫买鱼。
我却是喜欢买一竹篓一竹篓的鱼仔,省得打称,一竹篓都有三几斤重。各种意外的惊喜,各种认识的鱼都可以去发现去辨认:“凤尾”“赤翅”“金钱花”“三马”……就听那么美丽的名字,都会引起你无限的遐想。我每次都喜欢在里面找找还有没有新鱼类,就像发现新的宝藏一样,经常会有混进队伍的小虾小蟹,煮熟泛红就是装点了一锅汤的颜色。
买来之后,大一点的鱼,摘掉鱼鳃帮和鱼腹,洗干净,非常简单的操作即可,一锅下去煲汤。煲出来的汤水,鲜美绝伦,鱼汤是不用下味精的,加点蔬菜,或是加点葱、姜,下点盐,就是绝美的上汤了。营养丰富,容易吸收消化。
一个家庭主妇就是一部大百科全书,不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煎炒闷焗蒸煮,一条鱼也有一百种吃法,“靠海吃海”,真是其乐无穷。
家里人多的时候喝茶多,以为独自一个人时喝的茶少些,结果相反,独酌的茶如酒,时时刻刻都没间断。在广州的时候凤凰茶喝得更多更有滋味,这是令我意想不到的,因为在汕头时我是以福建岩茶为主打。现在反倒是潮州凤凰茶的味道更入心,这也是一种骨子里的乡思吧。绵延在血液里的茶汤,总归是需要家乡的山和云雾孕育出来,才能慰藉血液里的饥渴。就像海水里的族群,那种霸道的海腥味,才能与胃腺指认。家里翻箱倒柜寻找鸭屎香和蜜兰香,无意中也找出了两包来自大海的“蔬菜”:赤菜。
这种从汕头来的赤菜都产自南澳,那是一种海里的藻类植物,市场卖的都是干品。带着些灰白色的盐粉,赤菜呈熟褐色,潮汕人叫这个颜色为“赤”,“赤菜”的名称由此而来吧!有“树头”样状的枝桠,然后像树一样长出繁密的分叉,这浓缩版的树木长相,可以想象在海底的礁石壁上,它是如何像一棵植物般蓬勃生长,海水就是它的空气和风。
可能是由于采集艰难吧,据说要游到大海的礁石上,爬到那光滑的石壁上采撷,需要极好的水性和技术。所以赤菜很贵,一丁点儿就几十块钱。幸好干品的赤菜很轻,分量多,浸泡出来的赤菜像胖大海一样发胀得很威猛。
我们用三个指头抓一小把,放在杯子里,加上冰糖,用开水冲泡。杯子里的赤菜慢慢融化,用筷子或是勺子搅匀,变成很粘稠的东西,杯子里有沉淀的微小沙粒。喝起来清甜无比,很是解渴。自己调制无非多放了些赤菜,分量足,特别满足味蕾的需要,不仅清爽,还带着海的浪花翻滚而来,腥风和水珠,它们汇集在这个陶瓷杯子里,隔着千里之遥,舌尖可以感受到类似凝胶状的颗粒,它们更像是大海凝固的浪花。
因为这东西能健肠胃,以前朋友曾送给我一点,放在家里千般珍重,只有在孩子肠胃不适时才冲服。如今手头有两大包,于是放开大喝特喝。
作为食疗,应该平时常喝才有效果,防患于未然,“有病才医”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孩子这段时间脾胃不好,食疗胜于药物,我就这样冲泡给她喝,喝着喝着,自己忘了,肠胃毛病也好像丢了。
南澳的后宅鱿鱼据说也能消积(食积)。鱿鱼也是干品,要食用时先用水浸泡,最好是前一天晚上泡,隔天可用,切成薄片。白萝卜切段先煮,快烂时加上鱿鱼片。鱿鱼萝卜汤对小孩子食积很有疗效。潮汕人吃鱿鱼还有一个诀窍,即是浸泡鱿鱼的水不要倒掉,用这水去煮萝卜,熬出来的汤特别鲜美。我试过了,且一直这么做,后来在广州发现地道的潮汕人竟然都是一个模式出来的:尝过那鱿鱼汤的鲜美,绝对是海的原汁。
我嗜吃海鲜。这有点上瘾,如果一阵子没吃到,从胃到心,血液开始翻滚,它们要揭竿起义了,真像瘾君子。特别是腌渍过的海鲜,当朋友圈一个汕头的好友发了生腌海鲜的照片,我血液里的“海盗”终于醒过来,隔天我非赶一个有海鲜的菜市场买了生蚝,自己腌一盘海味来满足胃。
腌海鲜必须海产特别新鲜,为了十足的保险,我必须自己腌,一者新鲜,二者口味合适,最起码不那么咸。汕头的海鲜品种繁多,什么螺啊贝啊都可上盘当菜。有一种壳很薄的叫“鹩鹪”的,就是腌渍的上品。买来的鹩鹪先放在水里养,让它吐净沙子。然后用剪刀剪去两瓣壳之间突出来的韧带,这样腌出来它才不会“开口”。用粗盐腌渍个把钟头,中间还要不停翻转。倒掉腌出来的水分,加上酱油葱末辣椒蒜瓣再腌渍。味道已经出来啦!就这佐饭佐菜,比什么都可口,一瓶能吃上好几天。
而腌渍墨鱼就更容易。把新鲜的墨鱼掏去墨和内脏,洗尽、晾干水分,用大把大把的盐腌渍,装在瓶子里,什么时候吃就拿一点出来,蘸点辣椒醋,特别下饭。腌渍虾子的原理相同,你随便问一个从海边来的大婶,她都会给你说上美美的几道腌品。沿海的人,他们都习惯自己腌海鲜,这是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佐料,可以在时间的沉积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菜式。
正因为如此,潮汕盛产各种腌渍小菜,家家户户都会来一两种“杂菜”,这也是亚热带天气下保存食物之法。特别是容易变质的海产,加点盐腌渍能够保存几天甚至更长时间。
一个个腌渍瓶子里,它们装的是海!带着咸咸的海风。
□鄞珊,作家,二级美术师,出版《刀耕墨旅》《草根纸上的流年》《尘间·扉》等,现居广州。

![[致富经]螃蟹进棚 凭啥3个月净赚500多万元 20161220](https://www.aipiwu.com/uploads/20231206/1701852808969_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