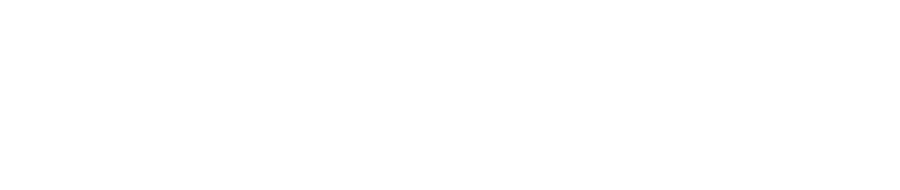“那群混小子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去各家屋外头听墙角,比较谁家父母晚上的耗时更长,碰上自家‘开车’,顶多就是骂声晦气,但听还是要听的。”

“······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全市普降中到大雪,24h降雪量已达5.4毫米,雪天路滑,开车出行的听众请注意路况······”
我爸正在后视镜里打鼾,我就关掉了车载电台。
我妈就不打鼾,打了我也不知道,自打上小学之后,我就没和她一块睡过。
桐山人离婚后,男孩都让父亲带,说这样才有男子气概。至于最后能不能有、能有多少,既没人调查,也没人关心,孩子长歪等于古人种菜,全看天意——我和我爸在后视镜里一对比,能看出来,天意并没站在我爸这边。
凌晨开车的困意很快战胜了医学生的自省。我戴上无线耳机,把车窗溜了条缝,从我爸包里摸出一盒五块钱老红梅,刚点上,我爸闻着味儿就醒了。
“啥毛病啊你,你差那五块钱儿啊是咋的?”
“就拿盒烟,看你那抠嗖样。”
我爸没好气地哼了一声:“抽我烟还有理了?”
我揉揉脸颊挤出个笑脸:“嗐,多大点事儿啊,等我买一条还你还不行吗?”
他没再说话,把后窗摇下来,被扑面而来的雪花星子和北风灌得直打喷嚏,只得作罢,跟我一样只留条缝透风。都说父子能一起抽烟、喝酒、踢球、吃烧烤······据我所知,大部分父子连完整聊够五块钱的都难。
“咱几点能到?”后视镜里,他正把抽了一半的烟头丢进烟灰盒捻灭。
“得一阵儿呢,九点半左右吧,要是困了你就再睡会儿,到地儿了我叫你。”
“刚才睡够了,现在倒是有点饿。”
我把车停在路边,刚想打开外卖软件,一抬眼正瞅见道边有推车卖烤冷面的,就下车跑过去买了两份,一份加蛋加肠加肉松加板筋,另一份正常做,两份都不要糖。
等餐的间隙里,我遥遥地望见桐山大桥那边有簇火光猛地冒了一下,但很快又被雪幕遮住了。
大概是出车祸了吧。毕竟是隆冬凌晨,又是这种鬼天气,出事儿也正常。
带着两盒烤冷面回到车上,还没来得及擦干雪水,我爸就把那盒大的抢走了。我没吱声,只是通过后视镜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神情从窃喜滑落到失望。
“咋样爸!没给你放糖,上年纪了别吃太多,不消化。”
看他郁闷的样子我更想笑了。这可不怪我,是刚才摊主装面的时候放错了盒子,他自己抢这一手,反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估计是真饿了,小份烤冷面在他手里连两分钟都没撑过去,我又把那份根本没打开的小盒递过去,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不吃?
我用力拍拍早已没了腹肌的肚子说,减肥呢,不吃,都是买给你的,你抓紧吃,咱们吃完了好继续上路。
我爸给了我后脑勺一下,骂道,上什么路上路,多不吉利。
我揉了揉脑袋说,你还信这个呢?
我爸边嚼着烤冷面边含混地答道,人老了,总得信点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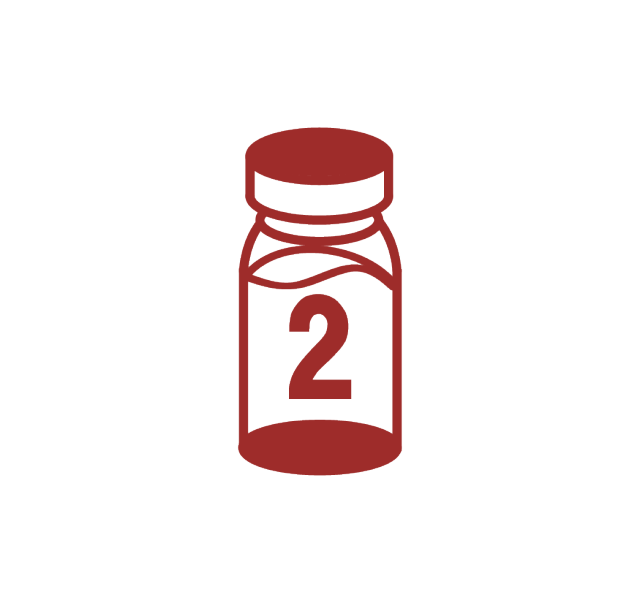
我爷爷当年也是这么想的。
即便是现在,桐山市的老城区里还有不少挂着药厂名头的地名——老药厂小区、老药厂饭店、老药厂公交站、老药厂医院······甚至几乎可以说当年的半座桐山市都是桐山药厂及其附属区域。
住过老式家属楼,或者看过电影《地久天长》的人都应该知道,那时候的人都没啥秘密可言,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墙体隔音连隔壁晚上办了几次事儿都听的一清二楚,就更别说其他了。
那时候我爸他们那群混小子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去各家屋外头听墙角,比较谁家父母晚上的耗时更长。时间久了,就难免偶尔会碰上自家“开车”,但他们也顶多就是骂声晦气,但听还是要听的。
后来事情败露,全家属楼男孩子的屁股都遭了灾,三天之内能下床的都算自家老爹手下留情。半个厂子的住户都开始找罪魁祸首,一开始男生们还念着点江湖义气死不开口,可到最后到底还是都没熬过冰糖+擀面杖或红糖+扫帚的组合拳,纷纷说出了同一个名字:卫长城。
要是找不出,或者最后发现是个普通人家的小孩都好,大家可能最多要么骂一阵子,要么打一顿就完事了。偏偏卫长城这个名字一出,却让很多被听过墙角的家长心里犯了嘀咕。
不为别的,因为当时桐山药厂的厂长叫卫汉业,而卫长城是他唯一的儿子。
没人反映,但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我爷爷耳朵里。他把我爸叫来,还没等开口,先上去就是一顿乱披风棍法,当时整栋楼几乎都听见了我爸的惨叫声,甚至有些人还以为是厂长家晚上杀猪了,还端着饭盆找上来讨几块猪肉尝尝。
其实这事儿到这就差不多算结束了。大小伙子嘛,谁还没有个荷尔蒙过度分泌的时候,再加上这教训也教训过了,大多数人就都很快忘了这码事。
但我爸没忘,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那天的毒打,老爷子根本就没给他解释的机会。不管别人说什么,自家父亲的粗暴和不信任,都让他对家庭彻底失去了信心。
他开始离家出走,学也不上了,活也不干了,跟古往今来所有叛逆的儿子一样,装出一副混吃等死、不干好事的混混模样。
他那时候其实特卑微。一开始我爸单纯就是想气一气自家老头子地作死,却没想到爷爷知道后却异常冷漠,根本就不理他;后来他急了,开始变本加厉,甚至还进过局子,可收到的反馈却是更大的冷漠。
我爸终于彻底失望了。
他换掉身上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也擦掉脸上不伦不类的妆容回到家里,开始了一场父子间长达六年的冷战。
这场冷战一直持续到1996年的下岗潮爆发。作为“末代厂长”,我爷爷回天乏术,在厂子倒闭前,他终于先摊牌了——相比于保住职工,他更希望能给我爸留下一条后路。
他没想到的是,就像当初把我爸的“丑闻”传到他耳朵里那样,他的这个决定也很快就闹得全厂皆知。眼瞅着局面就要控制不住,我爷爷辗转反侧了一宿,刚想自己出面解释,却没想到被我爸抢先了一步。
那天恰逢市里新落成的舞厅剪彩,全厂几乎有一半的职工都去看热闹了。可谁也没想到,出现在剪彩台上的,除了那个大腹便便的南方商人,另一个居然会是卫长城。
舞厅开业爆满了三天,卫长城就在里面唱了三天,以桐山电台兼职驻唱的身份。
据说,当时点播率最高的两首歌均来自药厂前先进个人、厂长卫汉业之子卫长城。
一首是他独唱的《红日》。
另一首是他和一个外地女生合唱的《最浪漫的事》。
这个女生叫魏莱,是当时整个桐山电台里长得最好看、声音最好听的女播音员。
后来她成了我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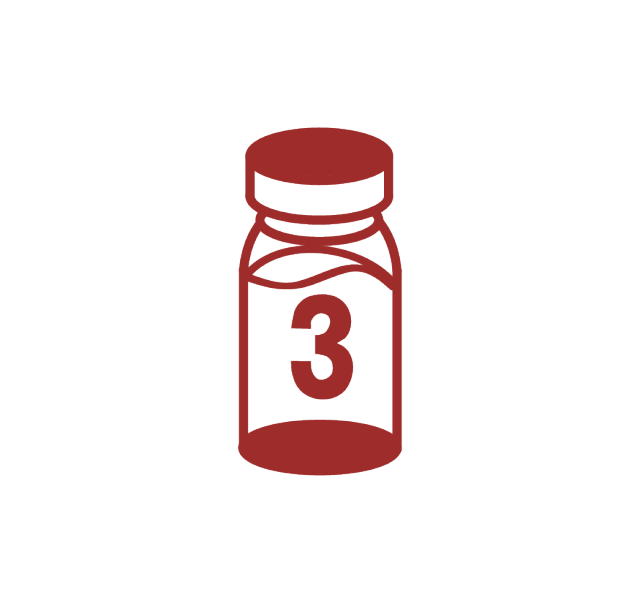
等红灯,我打开车载音响,里面是一首老歌。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音响有些失真,一段副歌过去,我才听出声音耳熟,进而确定演唱者正是我爸妈。
我是没想到我妈现在还会听他俩当初合唱的歌。
我爸估计早听出来了,一直没吱声,我没敢回头,用手指了指音响,说,还听吗?
我爸叹了口气,说,放着吧。
我突然有点好奇,就问,爸,当年爷爷和姥爷不是都说,你俩要是结婚就跟你们公开断绝关系吗?
我爸小声嘀咕着骂了一声,说,这些事你都哪儿听来的?你妈跟你说的?
我说,哪能啊,我妈能跟我讲这个?
我爸说,就那些老顽固,成天就知道耽误下一代······
我插嘴道,啧,听听,你说这话自己良心不会痛吗?
这话刚一出口我就感觉不妙,这么赤裸裸地戳他伤口肯定没好下场,但我这边刚一缩脖,却发现想象之中的巴掌根本就没落下来。瞄了眼后视镜,我爸裹着大衣,身子又往下滑了一截,整个人都缩在后座的阴影里,别说攻击性了,那模样一瞬间甚至都让人有点心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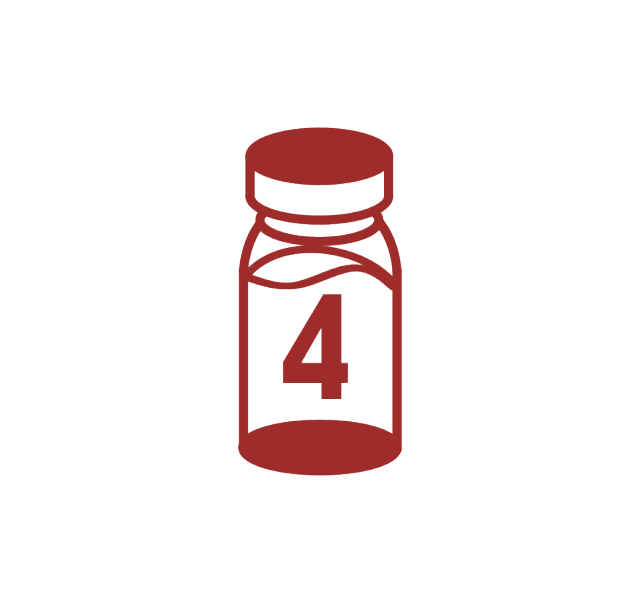
正式离家独立后的前半年,我爸的小日子倒还确实过得不错。可那时候毕竟是下岗潮,各行各业的年景都不好,我爸平时还得上专业课练声,再加上买最新潮的歌曲磁带又不少花钱,一来二去就捉襟见肘了。
幸亏他长了一张酷似平平无奇古天乐(黑古)的黑脸。
90年代末到千禧年初,人们的审美还没被选秀和白嫩的小鲜肉荼毒,我妈那时候会看上我爸也不奇怪。
他俩当时穷到只能合吃一份盒饭,感情却很好。我爸会趁工作间隙赚外快,给我妈买大宝和金嗓子喉宝;我妈也会趁单位发米发面的时候,把她自己那份换成几两肉晚上回家加餐。
一来二去,没等着结婚,就先怀上了我哥——年轻人嘛。
那时候哪有什么同居和不婚主义之类的概念?一男一女长时间交往,甚至连孩子都有了,却始终不结婚,那就是耍流氓,就是白嫖,就是不正经。当年的流氓罪可是口袋······算了,再说要不过审了。
总之,这件事直接惊动了两家长辈,他们纷纷下达最后通牒,说你们赶紧分手,孩子也打掉,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不然以后我们就没有你这个儿子/女儿。
但他俩到最后也没屈服。
恋爱之所以被人推崇,是因为看不到未来;而婚姻之所以被人诘难,也是因为看不到未来。
考虑到社会风评和小两口接下来的生活,他们还是决定先把证领了。
婚前体检是个女医生做的。领报告那天,30多岁扎着长马尾戴着方框眼镜的女医生面无表情地坐在桌子里,像极了高考时最严格的那类监考老师。
她说,女方没啥问题,就是长年节食,营养有点没跟上——但那时候一般人家都这样——这段时间记得多吃点好的就行;至于男方嘛,赶紧把烟戒了,抽烟有多影响胎儿健康你是不知道吗?
医生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无意间的一句话,往往就会决定一个家庭、一对夫妻后半生里的家庭地位——反正后来听说我妈扔我爸烟盒的时候,他连个屁都没敢放。

红灯转绿,我打转向灯从红旗街右拐,进入安平大道,等再过了桐生大桥,就算快到地方了。
我爸翻唱的《海阔天空》正到副歌部分,上一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刚高上去,结果后一句“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瞬间就低了好几个八度,听着还挺有趣,我就学着DJ那样反复地调节音量,一时间竟有种罪恶的快乐感。
由于还在开车,我玩了一会儿就把音响关了,我爸也没理我,还像个鼹鼠似的缩在后座上。
前年跟我妈见面的时候,她就又念叨起我和我爸,说你爷俩现在过得有啥意思,一个两个都是闷葫芦,在家待半个月就能说上不到半天的话,要是你哥还在就好了。要不,你抓紧找个女朋友带回来看看?
要不怎么说我妈当年能考上大学呢。你看这话说的,前半句还是群体aoe并将主要矛盾指向我爸,后半句就杀个回马枪问出了她最关心的问题:有对象了吗?
我说,找着呢妈,我才大二,还来得及。
我妈说,来得及啥啊,你没看别人都说大学毕业就找不到真爱了吗,你们现在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等你毕业了出来就没有真心了······你能不能上点心,抓点紧,不是说参加广播站了吗,里面有没有好看的······
我赶紧打断我妈的连招,行行行,我这把大四开学回去就找行不?就找那种比你嗓音差一点的,形象丑一点的,脾气臭一点的,你满意了不?
我妈说,你也就在我面前劲儿劲儿的,真要碰着人家姑娘,你还不一定敢说话呢。
讲真,我但凡以后在哄对象上有半点天分,都肯定是从小跟我妈周旋练出来的。
车开到桐山大桥桥头的时候,我终于近距离看到了之前我遥遥望见过的车祸现场。刚才远看只是风雪中一闪而过的小火花,近看还挺真惨烈的。清雪车正在桥上清道,我就拉上手刹,把车停在路边,独自下来问了问车祸的事儿。
虽然有点不尊重伤者,但确实挺搞笑的。
造成这场车祸的原因很简单,无非就是雪天路滑,加上视野不好,一辆小面包撞了一辆神牛(桐山本地人对人力三轮车的爱称)。但好笑的是,这里的肇事双方居然没有任何无辜者,神牛是闯了红灯,且还是违规改造过的,由人力改为了电瓶,结果被撞翻后引起了爆炸起火;而小面包就更搞笑了,虽然它没有闯红灯,但等它一头撞上路牙之后,却从车里下饺子似的滚落出八九个人——非常明显的超载。
要不是大早上就被这伙人逼着出警,我估计这会儿连交警都得憋不住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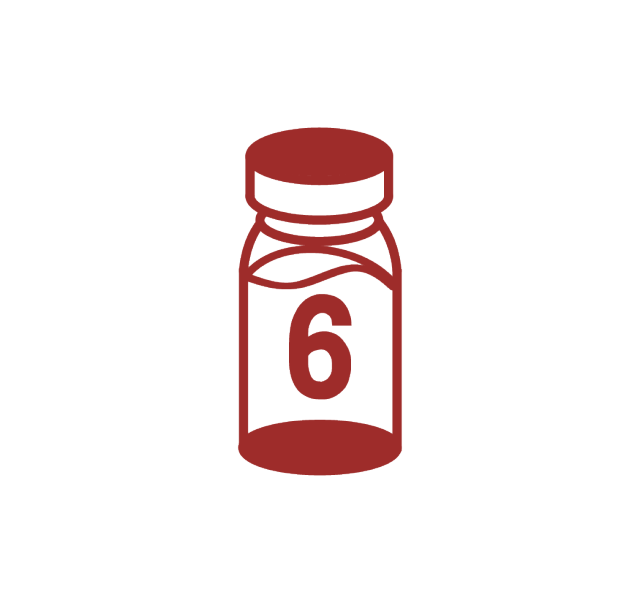
但我爸估计笑不出来,他从来都不喜欢坐神牛。
一方面他嫌神牛又慢又危险,说坐这个都赶不上去骑自己那辆除了车铃不响哪儿都响的大二八;另一方面他也听不得蹬神牛的师傅呼哧带喘的声儿,说自己可不是旧时代那些大少爷小少爷,没法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别人的劳苦。
可在那个生产力水平还远远没法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的时期里,神牛无论是作为代步工具还是运货工具,都至少称得上一句性价比之王。尤其是碰到雨雪天气,打出租太奢侈,步行或骑车又难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它就成了桐山人民的不二之选。
我哥的预产期是年关前后,正是台里最忙的时节。我妈又是台里的三大台柱之一,她的《小魏说事》栏目多年来都没掉出过桐山八点档收听率排行榜的前三,所以即便挺着个大肚子,我妈也还是坚持上班挣奶粉钱。
那时候内卷还不严重,我妈的人际关系也比我爸强得多,每天上班除了必须完成的本职工作外,杂事倒也没人来烦她,甚至她还被不少的女职工暗戳戳地羡慕着。
毕竟不是谁上下班都能有“古天乐”骑车接送的。
过年前一天,就在大家都打算加班加点把节目录完,好第二天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妈却突然倒在了演播室里。几个结过婚的女同事上前一摸,完了,羊水破了,赶紧送医院吧。
话说得简单,那时候晚上可没有滴滴打车,也没有那么多出租车,更何况又是过年前一天,外面还下着大雪。迫于无奈,众人只能先叫了辆神牛,钱都是台长垫付的,要求就一个,抓紧上路,但一定要安全地把魏莱同志送到医院。
说到这儿你们应该也能猜出来了,这一趟肯定出过事,不然我爸也不会那么讨厌神牛。
大路滑,再加上神牛师傅也看不清前路,刚过了桐山大桥,就一溜烟滑出去几十米后侧翻了。陪车的闺蜜为了保护我妈,搭上了左手的三根指头,至于我妈就更惨了。
我哥甚至还没来得及和这个世界打声招呼,人就先没了。

随着时针缓缓滑向数字9,雪终于小了点,也能看见天光了。
清雪车从桐山大桥缓缓开下,交警们也撤掉路障,开始放行过路车辆。
我回到车上,先看了眼我爸,他终于不再蜷缩着,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车外头那一地交通肇事残骸。
我说,别看了,爸,不吉利。
我爸说,别哔哔,开你的车。
天知道我关心他干什么,我此刻的表情想来一定像极了地铁老人手机的那张经典图片。
发动车子过桥,桥面上没什么车,钢筋铸成的斜拉索牢牢地连接着桥身跟梁架,双向四车道宽阔无比,路上的雪也刚被清空,整座桥干净到让人觉得有些诡异。
这座桥差不多跟我同岁,都是90年代末竣工投入使用的,属于当时最流行的32索H型双塔斜拉桥,跨径783米,正好连通了南北两个城区。说来好笑,2018年之前根本没人愿意去新区,全市的政治、生活和经济中心全都在南面的老城区,北边除了市电台、市公墓和市监狱外,就只有几处始终处于开发期的楼盘,下班时间一过,几乎没有任何人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18年后,等省里把桐山新区划入开发序列,才用了不到四年,江北的繁荣程度就已经远超老城区了。
我说,爸,快到地方了,你看眼东西齐不齐整,要是有啥缺的到时候我直接开车去买。
我爸这回倒没再怼我,只是弱弱地应了一声,又继续盯着桥上的斜拉索出神。
就在快要下桥的时候,我爸才缓缓说了句,青子,你也少抽点烟吧,不好。
我说,我也就抽这么一回,不信你问我妈,啥时候看我身上带过烟?
我爸也笑了,车里瞬间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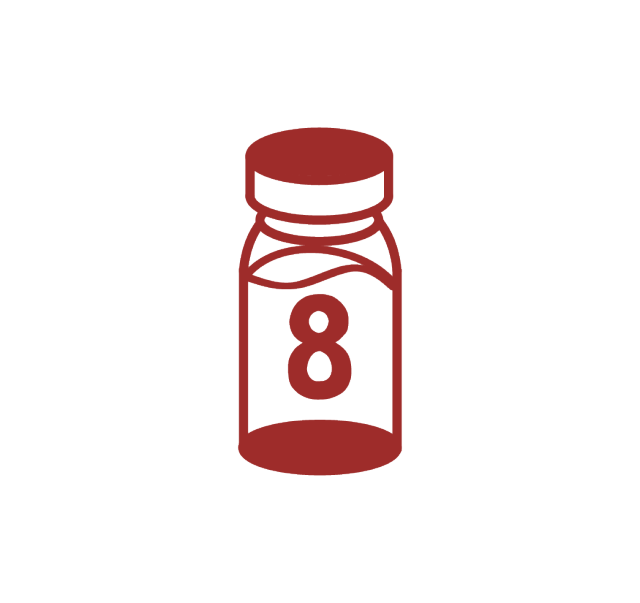
我知道,我爸说的“不好”跟吸烟伤身无关,我只是不想正面回应他而已。
做儿女的,面对父母装傻充愣这招,基本都是人生这本教材里从必修一就在自学的技能。
抽烟对身体当然不好,上面婚检的医生也说过了。但我爸嘴里的不好,显然指的不是这个,而是另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整个人生轨迹的大事。
婚礼。
很多男生从小就被灌输过这样的观念:婚礼,就是一个男孩变成男人的关键仪式。你有了家,有了媳妇,很多决定和行为就不能再冒昧轻浮,很多事情就要多考虑责任和义务,很多朋友和人就不能再过多接触——尤其是异性好友那种。
但我爸对此就一个字,屁!他从小就不喜欢束缚,不喜欢权威,对按部就班的世界也始终抱着某种傲慢与偏见。直到遇见我妈,他才甘愿折了腰平了毛上了紧箍。
说起来,我大舅二舅也都跟我爸差不多浪,当初也是敢在群架里带头冲锋的主儿,好就好在他俩有我妈这么个妹妹管着,哥哥的天性加上妹控的属性,倒是让他们后来的性子温柔了不少。可当我妈不在,这仨人又聚在一块的时候,就难免会造成点难以预料的事故。
99年的江北还没那么发达,别说婚礼场地了,连个适合聚众吃喝的饭店都难找。但大家秉承着来都来了、办都办了的宗旨,还是我妈出面说通了台长,借到了电台里唯一的宴会厅。
借到了筹备资金,又借到了婚礼场地,我妈就仁至义尽地提着婚纱跟着俩闺蜜伴娘去琢磨妆容了,现场的布置就留给了我爸和两个舅舅操心。电台的宴会厅在那时候也不算小了,一百多平的面积,舞台占了一半多,台下还能摆上个七八桌,对付他俩的小型婚礼绰绰有余。
仨大男人折腾了整整一天半,直到从摆花到礼花,从红毯到门毯,从花童到门童等等事项全都安排妥当了,这才一起瘫坐在放着婚礼烟花和物料的小仓库里。
我爸说,妈的,结个婚可真累。
大舅拍了拍我爸肩膀,说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这才刚结婚,以后的倒霉日子可长了去了。
我爸说,要是我明天笑不出来,一定跟魏莱说是你害的。
二舅说,行了行了,别扯淡了,你俩是真不累啊。谁身上带烟了,来一根?
我大舅走形式般的摸摸兜,说了句没有,他的烟早就被我大舅妈没收了。
俩人看向我爸,我爸有点脸红。他磕磕巴巴地说,婚检医生让、让我少抽点烟,说影响精子质量······
他声音越说越小,两个舅舅的笑声越来越大。
笑了一会儿,我大舅突然板起一张脸,故作严肃地对我父亲说,卫长城同志,婚姻就是监狱,抽吧,再不抽没机会了。
我二舅更是连话都懒得说,直接上手在我爸兜里摸出了烟盒和火机。
他摸了摸烟盒的手感,调侃道,行啊长城,都抽得起软包华子了?
我爸骂道,去你大爷的魏老二,这烟是台长昨儿塞给我的,我工资都在魏莱那儿,哪买得起这个。
舅舅们熟练地磕出两根抽起来,我爸也想抽,不过还是忍住了,没伸手。
戒过烟的人都知道,能下定戒烟这个决心本来就很难,再加上还有俩人在你面前不停吞云吐雾······这谁能忍得住啊?
我爸还是保留住了最后的体面——我就闻闻味儿,不真抽。
经典的男人式掩耳盗铃。
但事情坏就坏在他没真抽这件事上。老烟民都有个习惯,只要烟在手里,人走的时候不管抽没抽完都会下意识地捻灭烟头;可要是烟不在手里,很多烟民就会下意识地忘记烟头也算是火源这码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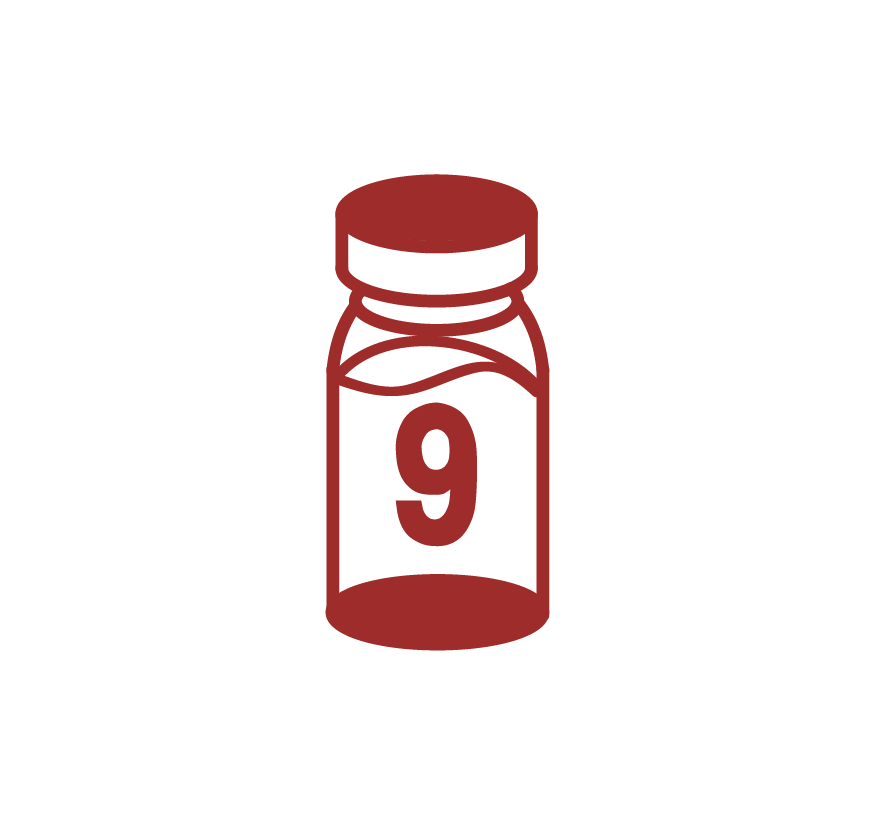
万幸,火势并不大,再加上那时候外头正下着大雪,所以没怎么造成太大的损失。
我妈听说这边着火,妆也不化了,伴娘也不管了,连裙子都没顾上脱,裹着件大衣就来了,直到看见我爸和俩舅舅都没事,这才放了心。可心放下了,怒气就上来了。
我妈是怎么怒斥我爸的,就不过多赘述了,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整件事到这儿却有了个有趣的转折。
火势是被控制住了,但准备给婚礼用的礼花却提前被点燃了。
这次的礼花都是那种炸出来形状特别好看的,我爸还定制了一个炸出来是我妈姓名首字母的高级货,但它们都没来得及活到明天晚上。在阴沉沉的大雪天里,别说看见高空的烟花了,能看见那簇升天的火星都算是运气。
现场一片混乱——烟花爆炸声,人群喧闹声,灭火器喷射声,车辆警报声······就在大家都忙着的时候,我爸哐地一下就给我妈跪了,单膝。
他从兜里摸出婚戒,轻柔地扯过我妈的手戴上,然后又站起来,搂住我妈,在她耳边低声说:媳妇,来不及了,事已至此,咱这婚礼就先这么凑合办吧。
又偷亲了一口,我爸随即撒丫子狂奔离开了现场。又过了十分钟左右,直到电台附近的大喇叭响起,我们才知道他到底去干嘛了。
“喂喂喂,123,123,魏莱同志,魏莱同志听得见吗?
“咳咳,我是卫长城。那啥,趁公安同志还没到,我再最后说两句。
“我这辈子大概就是那种啥也干不成的人,但老天爷也不知道咋想的,把你送到我面前了。说实话,你挺亏的。就像今天这种事,但凡是个正经新郎都干不出来······
“之前我爸总说我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我那时候逆反嘛,就寻思做成件事让他看看。谈恋爱也好,做电台也好,其实最开始都不过是跟我爸怄气。但跟你相处的时间长了,才发现这些事居然还真挺有趣,虽然不咋挣钱吧,但跟你在一块心里就热乎。
“前几天我妈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我说不知道,早都习惯了,咱俩一块吃过苦,一块挨过饿,最起码的革命友情还是有的,对吧?
“接下来该说正事了。也别等司仪了,我就直接来吧。魏莱,我爱你,无论贫穷疾病富裕啥的那些,然后是啥来着,对,我愿意成为你的丈夫。你那边就随意吧,时间不多了。
“最后,媳妇,你没看着那些烟火真的挺可惜的,有几个是真挺好看的。我还订做了一个带你名字的,现在估计早就放完了······”
如此离谱的结婚誓词,估计也就我爸才能面不改色地念上五分钟。
更离谱的是,我爸当时开的还是全城公频,也就是说,当时在听本市电台的人,都亲耳听见了我爸上面的这段“告白”。
我妈每次说起这事的时候总是有点哭笑不得,还跟我说你千万要多读书,尤其是多读读王小波那种,到时候结婚可别像你爸似的,丢死人了。
确实,就他当年这操作,词语贫瘠的我只能借用李安导演的那句名言:
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下了桐生大桥,我继续往北开,远离那些鳞次栉比的新建大楼和新式住宅区,驶向那座桐生市最北端的北山公墓。
墓园建在桐山阳面,十多年没翻修过了,嵌在一片光秃秃的山上显得灰扑扑的。
我爸因失火罪入狱的那几年里,我爷爷的墓都是我妈和两个舅舅来扫的,结果等他出了狱,离了婚,又跟俩舅舅因为钱的事儿干了一架之后,扫墓这事儿就只剩他自己来了。
现在又多了个我。
摆好带来的水果和贡品,烧了纸,上了香,我和我爸分别在我爷爷墓的左右两边坐下,远眺着脚下的桐山市。
桥南边都是一排排五六层的矮楼群,偶尔中间夹杂着几个大家伙——那是最初一批建起的大型购物中心和市医院,全市最长的一条货运火车线从东南角进入,穿过我家附近的铁道小区,拐个弯又从西南角钻了出去。那儿的居民甚至不需要闹钟,每天只要听见火车的汽笛声响起,就知道该起床做早饭了。
桥北边则大多是些新建成的联排小别墅区,以及各种十七八层的写字楼,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桐山市的新地标、高达三十六层的金龙大厦,它恰好就盖在原先的旧地标建筑——市电台边上。
我爸从供品里挑了个模样还过得去的苹果,咔嚓咬了一口,跟我说,吃啊青子,别浪费了。
我也顺从地摸了个大果,没吃,就拿在手里盘着。
我爸嫌弃地说,你搁那儿盘包浆呢。
我说,你就欺负爷爷吧,到时候我可不碰你的供品。
我爸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说卫青,没想到你这么迷信。
我说,卫长城,咱一码归一码,你不也是给我起了这么个破名。
我爸说,卫青咋了,卫青可是大将军,放我们那时候妥妥的TVB时代剧主角名。
我说,对,那是放你们那时候,时代变了,大人。
如果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那父子大概都是上辈子遗留的孽缘吧。
我俩离开的时候,下了一夜的雪终于有了要停的迹象,阳光把我俩的影子映在地上,也把金龙大厦和市电台的阴影投到山上。
不多不少,都是一高一矮,一短一长。
第1036号档案 · 研究成果
每个男孩都认为,自己的一生应该像一首散文诗。所以,他们大多看不上父亲,觉得他像个走哪儿跟哪儿的影子,或者说,自己才是父亲的影子。所以,他们抗争父亲,也抗争世界。等到了父亲的年龄,男孩们才发现,自己的一生并不是散文诗,而是旧报纸。
每个中年男人都希望和父亲来一场对谈——不是现在的父亲,而是中年的父亲。若有这种机会,他们将不再争辩“谁是错的”,而会感慨“都是对的”。
—

(本故事系平台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字数:9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