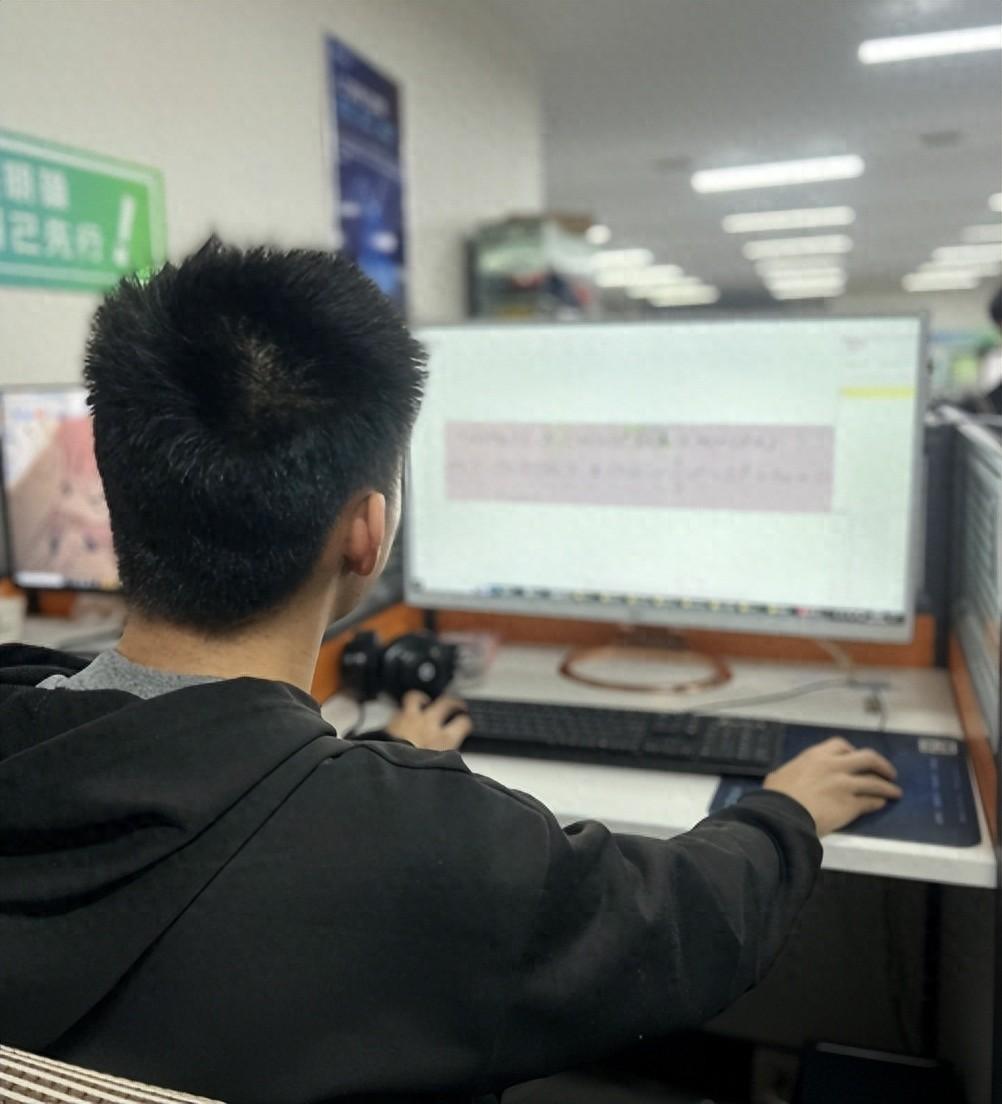前段时间非典闹的,关于食的话题特别多。作为一个广东人,在下尝过的东西想想倒也不少,不过对于那些稀奇珍馐可是极少沾边的,或者是心存善念,或者是财力不济,或者说还不到那个档次。
家在海滨城市,最常吃的是五花八门的海鱼,一天没鱼,就觉得餐桌上没菜,就差变成猫了(南方的猫吧?)。妹妹也特别爱吃鱼,而且总挑鱼头和鱼皮吃。夹上鱼头,美美的咂咂舌,说上一句我要和鱼亲吻了,一会儿工夫鱼头就隐形了。即便如此,在我筷子只能夹到鱼皮的回程中,妹妹的筷子也常常是倏然而至,把我的筷子紧紧夹住,那做哥哥的就只能发扬风格了。
爸爸还没平反回城的日子,除了拉拉胡琴,最常做的事就是到山上的小溪捉鱼,家乡话管这叫摸鱼。跟在爸爸后边,趟着清凉的水,那是我跟爸爸最亲密的时候。在山涧岩石里四下摸索,考的是足够的耐心和动作的机敏。有一次,老半天也没战绩,爸爸的腿倒是先让蚂蝗验血了。老家的人止血有高招,向人讨点烟丝在伤口上搓搓,革命还得继续。
相比每周的某一天六点多踮起脚尖冲着窗口里的大叔称我是某某老师的孩子,希望他刀下留情割点好肉的情景,我更喜欢山溪里的鱼被我们请到家里做客。鱼还没到嘴,光闻那锅里漏出来的香,都已经很满足了。那时侯总想跟爸爸做点交易:同意多画几张画(启蒙教育啊),让我多吃一口鱼。
吃着山里的鱼,吃着河里的鱼,再吃着海里的鱼,直到有一天,看到班里特别漂亮的女同学偷看我一如我看鱼的眼神,就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
有一段日子忽然远离腥味,那是我知道挑鱼还有许多学问的时候。
业已极乐远游、我极为敬重的东家曾是上层建筑的一分子,有一天酒酣之时,指点着盘子里的鱼,告诉我们时下场面上关于鱼的说法:
老婆是咸鱼,味道不鲜,但管饭,还真少不了。
情人是鳗鱼,味道肥美,但要拿捏得当,太用力,容易滑走;力不够,也吃不到。
欢场女子是河豚,土话音拐鱼,异常鲜美,刺激难忘,但处理不好,却容易中毒甚至身亡!
金鱼是观赏鱼,中看,但味道不咋样,养眼而已,秘书最好是此类,免得主人太过分神——后来许多有识之士也干脆不要“金鱼”了,一时男秘书特别受用。
那时候场面上的话真多,听得多了,才知道自己其实嫩得很。
比如有一年春节,一新任主管经济的要员捎着据说是其家乡特产的酥草鱼给素未某面的上层拜年,见面作揖:
身体傣傣。(傣傣,健康结实的意思)
钱银该该。(该该,很容易的意思)
姿娘栽载。(栽载,很多很多,姿娘即为女人)
这跟鱼没关的话题,打住打住。
挥别故土,京城里也有许多许多的鱼在游动。北方人确实独特,本来鲜活的鱼到了他们的手里却多是一个辣味。水煮鱼吃得多了,火气特别大。偶尔到广东菜馆解解馋,买单的时候则太容易感到手重。
罢了罢了,看来要策划市场还是得先从策划怎样食鱼开始。市场上的海鱼寥若晨星,于是,以前对付客户的三寸不烂之舌转而用来劝说鱼贩同意分开草鱼,然后将鱼头卖给我,好跟豆腐配合满足我。实在游说不了,则跟旁边的哪位水灵或慈目的大姐微微一笑,用颇具磁性的中音吐出北京朋友验收过的普通话,邀请协作瓜分整尾鱼。
这一招往往奏效,拎着鱼回到家擦脸的时候照照镜子,偷偷的为自己还拥有一张不讨人嫌的脸窃窃自喜!
武昌鱼是非吃不可的,甭说冲着那才饮长江水又吃武昌鱼的光辉诗篇,就凭着哪位同事特别是美眉的赞美,清蒸武昌鱼的氛围也就把自己的情绪蒸了出来。虽然体会不到伟大领袖的那种动感,但好象也长了几分豪情。
嗨,又快到下班时间了,呆会买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