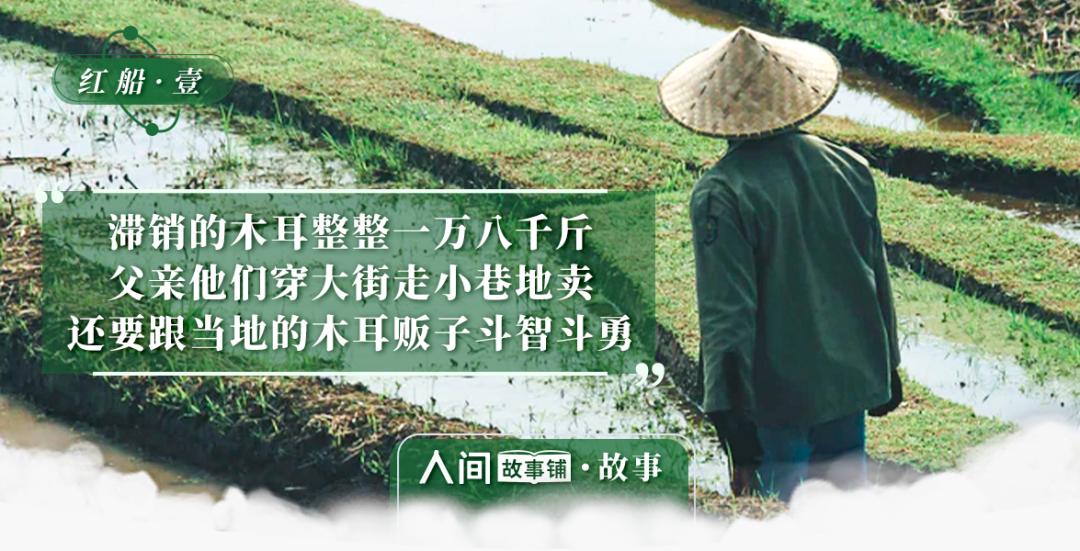原创 彼岸 人间故事铺 收录于话题#红船写作计划2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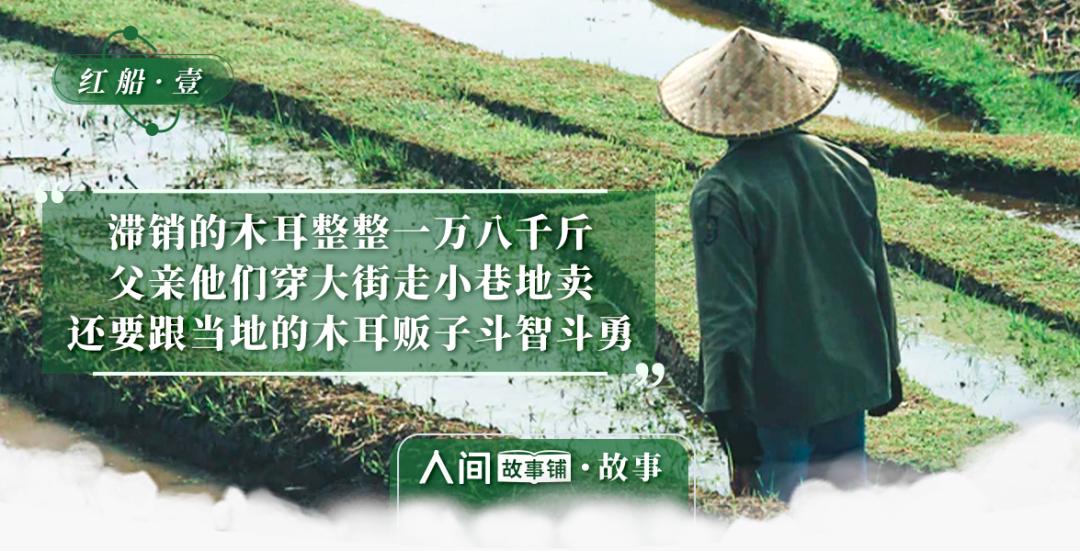
为了让生活好转,父亲抓住一丝希望,去北大荒打拼。扛下劳作的艰辛,顶着创业的风险,父亲一干就是15年,无数汗水化作前进的阶梯,带着整个村子走向致富的道路。
人间故事铺 X 红船
·hong·chuan·
1981年夏末,秋风渐起,在大连郊区一间简陋的平房里,父亲和四个村民沉默地吃完简单的早餐,便起身来到院子里。那里堆积着小山一样层层摞起的麻袋,里面是干燥好的木耳,总共一万八千斤。
每天,父亲一行五人挑着麻袋,走出他们临时借住的村民亲戚家,拐到街口,等待一趟去往锦州的客车。
“你们去南北街上吆喝吆喝,我去那边看看。”父亲支开了四个村民,独自走去了木耳需求多的街区,那里也是锦州当地木耳贩子集中叫卖的地方。父亲的售价比他们的便宜,早就激怒了当地小贩。父亲怕村民不会跟小贩周旋,吃亏受欺负。
再说,不在那片街区“打开市场”,这么多木耳怎么卖出去?
走进一条狭窄的小巷,父亲被三四个木耳贩子截住:“你一个外地的,敢跟我们抢地盘?大伙儿,上!收拾他!”小贩们怒目相向,围拢过来。
父亲不动声色,卸下挑着的木耳袋子,把肩头的大长棍握在手里,四下里一抡,大吼一声:“哪个不要命的,给我上来!”
几个小贩被震住,灰溜溜地走了。
这是父亲来到北大荒的第六个年头。

1975年农历二月初二,父亲虚岁28,婚后第二年。凌晨4点,父亲怀揣着35块钱,背着一床被褥一套棉衣裤捆扎好的行李,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奶奶昨晚熬夜蒸好的高粱面咸卷子窝头。在鲁西南的一个小村庄里,父亲告别爷爷奶奶和我的母亲,一路北上,开启了他闯荡北大荒的人生。
北大荒旧指黑龙江嫩江流域、黑龙江谷地与三江平原广大荒芜地区。据史料记载,1948年国家揭开了移民开垦北大荒的序幕,到了1958年,北大荒开始大规模开发,举国瞩目的10万官兵进驻北大荒,1959年5月至10月,又有6万山东支边青年从齐鲁大地开赴北大荒。七爷爷和九爷爷就在那一波潮流中从老家移民去了小兴安岭,后来定居伊春五营。
而彼时,1960年前后,山东老家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爷爷在麻风病院,奶奶饿得水肿,作为家中的老大,12岁的父亲领着大叔去要饭。16岁,父亲步行到200里外的曲阜进地瓜干,夜以继日地返回,奔去集会上卖掉。后来,父亲又半夜去煤矿排队买煤,拉到附近村庄去卖。
那时老家是生产队集体劳动,一块儿下地挣工分,一天只能挣两三毛钱,打下的粮食还要先交公粮、留种子,分到个人家的根本不够吃。我的祖父只有满腹学问,不精通农活,更不懂经营,全靠父亲想办法挣钱补贴家用。父亲悄悄买来稻草机,白天在生产队干完活,晚上打草绳,连夜送去县里联系好的一家土产公司,第二天让祖父赶到县城去卖。
一年后,家里的日子好转,可是那年开春,年年都分到的国家返销粮却被村里扣除。接着第二年,村里各家都开始打草绳,已经无利可图了。
就在这时,二爷爷家的明杰大爷捎来口信,邀请父亲前去东北。明杰大爷一年前去了大兴安岭的呼中姐姐家,干了一年拉大木,却没有挣到钱。但正好赶上在嫩江粮囤的亲戚要建点开荒,两人商量,第一个,开荒得有个会东北农活的,再一个,最好多叫几个老家人来,不孤单。明杰大爷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父亲。父亲在18岁时去过东北吉林磐石,学做东北的农活,学着学着,父亲就成了打头的,谁的农活也不如父亲。
除了父亲,明杰大爷又想到了大爷爷家的明义大爷。明义大爷在老家带工挖湖,三个月之后才能前去。
在明杰大爷找人给父亲办了准迁和粮食关系后,父亲便率先起程了。老家的亲戚朱姑姥爷要投奔东北甘河的亲戚,便与父亲同行。
两人要步行前去十里地的县城汽车站,然后坐汽车前往济宁火车站,坐上下午四点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再倒车去嫩江。火车票27块1毛钱,父亲记得很清楚。
迈进火车车门时,父亲踉跄了一下,背上巨大的包卡在车门处,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发力,后面涌进的人群就把父亲搡了进去。
车上人挨人,人挤人,地上都是行李,脚都没地方放。父亲在火车上站了一天一夜,到了沈阳北站,才有了座位放置僵硬的双腿。
火车呼啸,带领父亲走进了东北的广阔黑土地。积雪覆盖着莽莽草原,森林荒野无边无际。
△ 北大荒的冬季 | 作者供图
到嫩江已经是第三天的晚上了,朱姑姥爷继续前行,父亲下车在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夜,等待第二天早上明杰大爷的亲戚来接。
第二天正赶上垦荒办去粮囤办事,于是搭乘了他们的拖拉机。漫天的雪野,白得耀眼,拖拉机“突突”地在崎岖的雪道上颠簸着行驶,坐在后车斗的父亲迎着刺骨的寒风,“颠得像散架了一样。”
大约六个小时后,父亲抵达了最后的落脚点——粮囤。

粮囤坐落在四面环山的洼地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不远处驻扎着垦荒的部队,最近的村庄在五里地之外。在西山口处有一条山道,是通向外界的唯一出口。
安家就要先盖房子。父亲先用木头搭出来房架子,再往木头缝里塞黑泥,用榔头砸结实,最后房顶苫上草。大伙互相帮忙,一家盖完再给另一家盖。
但这样的房子根本不能抵抗零下四十多度的寒冬,屋里四处漏风,土豆冻得邦邦硬。而到了大风天,还要防备屋顶的草被大风卷走。常常是大风前脚走,雨点随后到,屋里不时地放着接雨的盆盆罐罐。
生产队去年产的粮刚够几户人家温饱,父亲吃了三个月土豆,一年只吃了二斤油。有一回,部队里养的猪长痘,死后被扔到野地里。父亲他们馋得不行,也不管得不得病了,偷偷拉回来,用大火炖了,吃得那个香啊。
部队已开垦出了大片的荒地,父亲和村里人只能在空隙里开垦,种上生长期短的土豆小麦和大芸豆。开春播种翻地用拖拉机,后期就得靠马或者牛,最开始用大刀打麦子,再用半自动的脱谷机,而黄豆只能用马拉滚子碾压。

△ 7月中旬北大荒一望无际的黄豆地 | 作者供图
这里大雪是常客,出山除了步行,大多使用马爬犁穿越镜面一样的雪地。到了积雪融化之时,高低不平的泥水坑最是泥泞难行。有一年,运土豆的汽车陷进泥地里,大伙开着拖拉机拖拽,竟然把拖拉机都拽翻了。后来产的土豆运不出去,都埋在土地里冻硬了,只能烀了喂猪。
除了严寒与荒野,山上还常有黑熊出没,东北人叫它“黑瞎子”。
第二年跟随父亲而来的母亲曾经历了一场黑熊闯院的惊魂事件。
那年夏天,夜半,母亲被牛叫声惊醒,听见院子里发出稀里哗啦的声响。和我家是邻居的明杰大爷养蜂,一排蜂箱摆满了后院。那天父亲不在家,母亲猜测是牛进了院子,便出去拍门叫醒大爷。
明杰大爷拿了手电筒往后院一照,母亲惊出一身冷汗,一只半人高的黑熊在强光下惊慌逃窜,一排蜂箱被踩翻,蜂蜜被吃个精光,菜地压倒一片。
第二年刚开春,就有两个村民上山被黑熊伤了,早先还有一个邻村的,被黑熊吃掉,肠子流了一地。
那年刚开春,山上都是积雪,村里两个人上山砍椴木。有个二队的李老师,光仰着脸找木头,猛然看见前面草甸子上有个黑包,还没反应过来,一个黑熊呼地站起来,一下把李老师扑倒了,一爪子就把他额头的皮掀起来一大块。另一个跑过来救李老师,拿着手斧子一顿乱砍,被黑熊抓伤了脸。
手斧子砍几下根本不管用。万幸的是,黑熊转身又卧倒了。两个人搀扶着,血葫芦一样,哭爹喊娘地跑下山去。大伙猜测,黑熊身下可能有小熊崽,才无心恋战。
父亲当着民兵连长,保管着十二支枪。被黑熊伤到的两人跑下山来已是黄昏时分,父亲就和几个民兵连夜赶着马爬犁请来了一个鄂伦春猎人,被人称为“邵枪手”的,帮忙猎杀黑熊。
第二天一大早,十几个民兵每人手握一杆枪,浩浩荡荡上山了。临行前,邵枪手叮嘱大家,听他的指挥,别乱开枪。
果然,黑熊还在老地方,有五六百斤。可能是因为昨天被惊到了,离了百米远,黑熊就“呜呜”地站起来,吼叫了一声,震得林子里树叶哗哗往下掉。一帮人吓得早把邵枪手的嘱咐忘了,拿起枪没命地一顿乱打。
黑熊受伤,打了个滚,往森林里逃走了,大伙一路狂追,追到下午两三点钟太阳就转西了,正准备返回时,又与黑熊“狭路相逢”。在距离黑熊七八米远处,邵枪手开枪,命中黑熊的胸口。邵枪手近前,拿出腰刀,剖开黑熊的胸膛,取出熊胆。大伙找到最初的巢穴,捉住了幼小的熊崽。
第二天,村民坐着马爬犁拉回了黑熊的尸体,全村吃了一顿熊肉,扒下的黑熊皮铺满了一丈长的大炕。三个熊崽却没能养活,陆续死掉了。
两三年后,粮囤已增加到六七十户人家,全村人总共来自七省十六个县,有黑龙江的、辽宁的、吉林的、河南的、河北的、江苏的、山东的……大多都像父亲一样是投亲靠友来的。也有的干了一年半载,受不了严寒和闭锁就搬走了。
父亲和村里人时刻琢磨着赚钱的办法。夏天时候,村里人去山上采蕨菜、蘑菇、猴头、木耳、榛子等等山野植物换些钱。漫长的冬天,父亲和村里人去给林场伐木,一百多根木头装满一车,能挣五六块钱。山上积雪深厚没膝,大家用手提锯子,一棵一抱粗的大树要锯上整整一天,汗把棉袄都浸透了,脱了扔雪地里,冻得跟雪壳子一样,拎起来唰唰响。

△ 大雪覆盖下的北大荒粮囤村 | 作者供图
有个二队的队长,开始在山上养人参。成熟的新鲜人参,煮了,扒去皮,晒成干参,能卖到100多块钱一斤,但人参生长期很长,五六年才会有收成。
当时村里有位姓陶的师傅养蜂,明杰大爷便跟着学养蜂。最多的时候,不算用来繁殖的蜂箱,光是采蜜的蜂箱就有五十多个。蜂蜜8块钱一斤,供销社专门来收。过不了几天,明杰大爷就去乡里拉回十个八个200斤的蜂蜜大桶。
父亲也跟着养了几箱蜂。但养蜂的活细碎而杂乱,父亲忙着村里的事,便没有扩大养殖。
后来,父亲在帮生产队去内蒙买牛时发现了商机,一头公牛100块钱,而用买公牛的钱能买三四头母牛,“母牛生母牛,三年五个头”,买来三四个母牛,两三年后便能拥有十多头牛。
在得知政府允许个人养牛后,父亲第一个贷款和村里人结伴去内蒙买牛。
父亲买回了三头母牛,有的村民也买了马,几百里地,父亲他们骑着马,边放牧边往回走,晚上就随便找个避风的地方歇息,整整走了两天。
而真正让父亲和村里人富起来的是种木耳。
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徐徐而来。
严寒将要退场,覆盖了一冬的积雪渐渐在太阳的热吻下融化,黑土地露出了它润泽丰沛的脸庞。
整个春天,父亲都是忙碌而充满希望的。院子里横竖摞满了截好的木段,它们尺寸相等,粗细均习,像用木头搭建成的方阵。仔细看,你会发现,段木是动过“手术”的,在每隔大约四指宽的距离,镶着一个个一分硬币大小的木塞。那里便是孕育木耳的巢穴。
到粮囤的第三年,政府号召农村搞副业,种植黑木耳,并派了各村干部到乡里学习种植技术,当队长的父亲是其中之一。
试种时木耳菌种可以赊账,山上有的是木头,不用花钱。种木耳虽然是技术活,但每个环节按照要求操作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辛苦,父亲是不怕的。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父亲觉得能行。
说干就干,父亲买了菌种,立刻拎着斧头去山上考察树木了。种木耳用的木头叫柞木,必须在三九天砍伐,那时候树木进入休眠期,树桨饱满,最适合木耳生长。
父亲把砍伐的木头用马爬犁拉下山,摆在院子里截成段,全部截完已经到了年三十的晚上,各家门前的红灯笼都亮了。
截好的木段先要一个个扛进屋里缓霜,然后打眼、按菌种,为了不耽误春耕,这些都要在开春之前完成。
第一年,父亲截了两个木耳段。隔几天,父亲便往“木头方阵”上喷喷水,早晚温差大,还要精心地苫上草保暖。天热了,木耳段便可以一段段摆开了,下面用木头担上,留有空隙,隔一两天就要翻下木段。
木耳段一年种,三年收,第一年初收(只有少量能采摘的木耳),第二年盛收,第三年罢收,夏秋两季都可采摘,视气候而定,夏季产量最多。
看到密密麻麻的小耳朵米粒一样探出头来,父亲知道他成功了。村民们也开始行动了,他们学着父亲的样子,伐木、打眼、按菌种。
父亲跑东家窜西家,挨家挨户地查看,提醒他们技术上的漏洞。
“你这咋整的,菌盖没消毒?记住了,放锅里煮,多煮会儿。”
“木段咋贴着地?那不进杂菌了吗?温室里长的能打过野生的吗?”
“想偷懒?那不行,喷水翻段一样都不能少,你懒,它就懒得给你出,最后坑的是谁?”
……
二队的老李哭丧着脸过来了,他贪多,种了七千木耳段,却有超过一半的段木像睡着了一样,毫无动静,这就意味着,这些段木全部报废,连本钱也挣不回来。
接着又有几个村民找来了:“这是咋回事呀,一段都没出,就跟着你队长学的呀。”
父亲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仔细抠。
最终发现还是技术不过关。父亲沉思,这样不行,得请个技术员来详细讲解。于是便从乡里请来了技术员,办了培训班,每天督促各家各户前来学习。
此外,父亲发现,还有一部分因为菌种不过关,有的村民图便宜,买了劣质菌种,却吃了大亏,父亲又为村民统一了购买菌种的地点。
雨季过后,天空放晴,仿佛突然之间,条条段木变身披着黑色花朵的花树,团团簇簇。村民们埋头采啊摘啊,一朵木耳就抓满把,一段木就能采满满一筐。
各家各户的院子里,磨盘上,屋顶上,木耳们不断被晾晒、翻动,直到发出干燥清脆的哗啦声响。
父亲开始盘算收成,一斤木耳8块钱,两千木耳段能收八九百斤,这样就收入六七千块钱。父亲比村民早种了一年,第一年的收入基本抵了赊的木耳菌钱,再加上第二年又新种的两千木耳段,轻轻松松成了万元户。
贫困的帽子摘掉了,父亲一下感觉腰肢舒展起来。

△ 1985年,父亲在家门前读老家来信 | 作者供图
带领村民种木耳的第二年,父亲被选为村长。
村民们大张旗鼓的砍伐引来了林场管理员,他们提出要收费,每段木要收1毛钱,这在当时收费已经很高了。如果细数,全村人有几十万木耳段,对于刚起步的村民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父亲按自己种的实际段木交了费用,其余村民的,父亲跟林业人员商量了一下,只大约估个数目交了费,但仍然给家中劳力少、贫困的村民增加了负担,有的连木耳菌种的钱也掏不出来了,父亲便以村长的身份给他们去信用社贷款。
村民们种植木耳的积极性像盛夏层出的木耳一样爆发。初春的凌晨,沉寂的大山深处,夜的美梦还没来得及收尾,就被一阵阵密集的像鞭炮炸响的噼啪声惊醒。那声音,在父亲听来,确实就像新年喜气洋洋的鞭炮声,美好的日子在前方闪闪发亮。我的村民要富起来了!
父亲满腔的激情鼓涨着,他把每年坚持书写的入党申请书小心地收起,踌躇满志地谛听了一会儿,也抡起大锤加入了村民们打眼的队伍里。
改革开放让人们的心思活泛起来,小山一样堆积的木耳吸引来了各处倒卖木耳的商人,可是,精明的商人把价位压得很低,农民得不到实惠,而对于大丰收的木耳产量,零卖费时又费工,父亲又开始琢磨出路了。
有个村民的亲戚在大连郊区,听说在大连纺织厂有规定,工人每人每天要吃四两木耳。父亲马上和那个村民跑去了大连,联系了当地纺织厂,发现工厂需求量很大,而且价格翻了一番,达到了16块钱一斤,父亲大喜过望,连夜赶回,第二天就开始统一收购村里的木耳,除了在大连有亲戚的村民,又选了两个精干的,雇了一辆大卡车。
每年的夏末,连阳光空气都因为欢喜而颤抖着,村民们满脸喜气,忙碌着把一麻袋一麻袋干燥好的木耳装进大卡车,满怀期待地望着大卡车远去。
这欢喜太过强大,掩盖了连父亲也没考虑到的变故。
井喷似的木耳产量让工厂的收购达到了饱和。1981年夏末,当父亲雇了一辆大卡车,长途跋涉地再次来到大连纺织厂时,被意想不到地拒之门外。
整整一万八千斤啊,怎么办?
零卖呗,能怎么办?就像他们最初种植木耳一样。父亲和同来的村民默契地甚至没有开口商量,就打开麻袋,把木耳分装成1斤的小袋,一麻袋装30斤。父亲记得,这成麻袋的木耳,很多村民都没有过秤,直接就装了车,他们信得过父亲。
锦州是距离父亲他们居住地最近的城市,往返有客车,省了住宿的费用。

△ 1981年,在大连锦州卖木耳,父亲和同去的村民合影 | 作者供图
那年,锦州的秋天来得格外早,父亲他们穿着单薄的衣衫,穿大街走小巷,还要跟当地的木耳贩子斗智斗勇。整整两个月,最后剩下没卖出的1000多斤木耳赊了出去。他们不能再耽搁了,除了家里几十亩黄了茎秆等待收割的黄豆,父亲为村民们担保的贷款也到期了。
到家的第二天便是还贷的日子。那天大雨倾盆而下,泥泞的山路积水成河,父亲心急得跳脚,这是头一回给村里贷款,失了信用,以后还怎么做事?父亲越想越严重,不行,就是下刀子也得去!
大雨之中,父亲披了雨衣,穿上雨靴,走了四十多里路,去信用社还了贷款。
信用社主任很感动,他告诉父亲,其实延迟几天也没问题的。事情传开后,县农业银行的行长亲自开口,又给贷了一笔款,到后来,只要打一个电话,父亲就能贷上款。
三年的时间,在父亲的带领下,全村只卖木耳就达到人均收入2000元。
作为带头致富的农村干部典型,父亲到乡里县里演讲,连续写了八年的入党申请被批准,后来又被破格提拔为副乡长,而我家也从粮囤搬迁到了乡里。
此时,父亲在粮囤整整待了十五年。

△ 1990年,我们在北大荒粮囤村最后的家,就在那年我们家搬去了乡里。| 作者供图
等我们都成家立业之后,父亲办了病退,日子轻闲下来,父亲有了落叶归根的想法。正好年迈的爷爷需要照顾,父亲就携母亲回了山东老家。
爷爷去世后,父亲和母亲便在姐姐所在的老家县城留了下来。
明杰大爷和大娘几年前就回了老家农村,东北的土地给了儿子打理。大爷翻新了老宅院,卧室里新砌的大炕透着一股浓浓的东北特色,让冬季的屋内暖融融的。明义大爷当年因为文化高,到粮囤不久就去学校进修,做了小学教师,后来又升为乡中学的校长,退休后跟着子女去了南方。
晨起,父亲溜达出门,买回他仍钟爱的老家的饮食,豆面粥、煎包或者烧饼、羊杂汤,吃饱喝足后带母亲去公园转一圈,健健身,或者去老朋友那里下一盘象棋。
过年过节回老家农村给爷爷奶奶上坟时,父亲总会提起当年离家时,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爷爷给的八字赠言——“但做好事,莫问前程”。
而今时的老家农村也非往日。父亲曾经用脚步丈量过的土路,早已变成通往家门口的水泥路,早先只能解决温饱的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被大片青绿的蒜苗覆盖,老家所在的县城已成为著名的大蒜之乡,罐头瓶口大小的蒜出口国外,年出口量达到百万吨。
近几年农村又种植了一种新兴的经济作物朝天椒。小叔在外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了农村老家,接手了家里的9亩田地,精耕细作,像种菜园子一样经营庄稼,最好的时候,晒干的朝天椒一斤能卖到六七块钱,一年两茬,大蒜和朝天椒轮流播种,一亩地也能收入万元。村里有年轻人的家庭,几乎家家都备有小轿车。
隔三差五的,父亲就骑着电动三轮车到农村老家的地头上转一圈,和明杰大爷还有姑姑小叔们这些老家的亲戚聊天,本来就带有山东口音的东北话彻底“山东化”,那些方言张口就来。但一回到东北,父亲立刻切换自如,操起他不太正宗的东北腔:“当年我混东北的时候……”
2015年年初,母亲去世,孤单的父亲越来越想念他的东北老朋友。那年夏天,姐姐带父亲来东北探望。

△ 2015年父亲回东北时,我家在北大荒粮囤村最后居住的房子还在 | 作者供图
父亲去了乡里后,曾和父亲一起去大连卖过木耳的老王当了村长,如今拥有上千亩地,全部包出去,一年收入四五十万,在县城买了楼房,过起了悠闲自在的老年生活。这些大量开垦的荒地都来自于1994年前后,那时,政府提出再造一个黑龙江,鼓励农民开荒种地,正当副乡长的父亲为粮囤争取了批地的文件。
粮囤还居住着四五家当年的老人,明杰大爷的大儿子做了村里的会计,同时经管着四五百亩田地。“现在大豆需求量高,国家鼓励种黄豆,一垧地光豆补就4800元,还有粮补油补各种补贴,不算地里的收入,一年光补贴就十多万。”父亲说。
还有养蜂的,一年也能收入四五万块钱。近几年,国家提倡退耕还林,早就不种木耳了。
“都铺上水泥地了,一溜儿的砖瓦房,种地全都是机械化,客车一天一个来回趟,两三个小时就到县里了。老人们还记得当年呢,各家轮流请吃饭,都念着我的好哩。”父亲颇感自豪。

△ 如今的北大荒粮囤村宽敞的砖瓦房 | 作者供图
2017年夏天,搬去秦皇岛享晚年的老刘邀请父亲和其他五六个老朋友去海边休闲。老刘当年很早就从粮囤搬到了乡里,在政府当了种植木耳的技术员,村里的木耳菌种都是从他那里买的。
几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聊得最多的还是当年在北大荒的日子。“当年的那个苦啊,都是咋过来的?”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吃苦哪来的甜?”
“那时候咋能想到有现在的日子,是国家的政策好啊。”
近两年,父亲每年夏天都来东北小住。去年,父亲在哈尔滨安家的我处停留。正准备好好款待父亲一番,转身见父亲从市场里拎回一袋大酱,一碗大碴粥和一把绿油油的小葱。父亲说,不要花费那些大鱼大肉的,他就想吃这个。
刚住了三天,父亲便急不可耐地要奔去他的“北大荒”。因为是暑期,父亲又来得匆忙,没订到卧铺。我劝父亲再待两天,看看有没有退票,或再想想办法。
父亲两眼一瞪,大手一挥:“就坐硬座,有啥不行的。”仿佛当年他闯东北的劲头。
题图 | 图片来自unsplash
配图 | 文中配图由作者提供